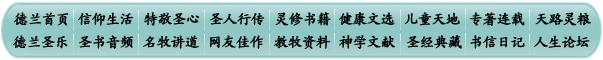|
仅将此书献份艾迪斯·威斯科波夫·晾李森,以纪念她早在1955年就在美国开始的探索意义疗法的开拓性努力。她在这一领域的项献是不可估量的。 让我们首先思考一下,应当如何理解“悲剧乐观主义”。简而言之,它的意思是,尽管存在着“三重悲剧”,人们仍然能够保持乐观。正如意义疗法所表述的,一种由人的存在的几个方而构成的三重悲剧可划分为∶〔1〕痛苦;〔2〕内疚;〔3〕死亡。事实上,本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面对这些痛苦时,人们怎样才能仍然表现乐观?或者以另一种方式提问,尽管生活存在着悲剧的一方面,但它还能保持潜在的意义吗?作为回答,这里引用我的一本德文著作的标题的一句话,“而对任何情况下的生活”。这句话假定人的生活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是最悲惨的情况下都具有潜在的意义。并且,这种假定会使人具有创造性地将生活的消极方面转化为积极的或建设性方面的能力。换言之,重要的是,在任何既定的条件下都能够尽最大努力。“尽最大努力”在拉丁语中被称为是乐观主义——因此,我提出了悲剧乐观主义,一种面对悲剧的乐观主义,并认为人类具有三种潜能∶〔l〕把痛苦转化为成就;〔2〕从内疚中获得完善自我的机会;〔3〕从生命的短暂性中获得采取负责性行为的动力。 然而,必须牢记的是,乐观主义并不是可以随意命令和调遣的东西。人们甚至不能无视各种可能,对抗各种愿望,任意地强迫自己保持乐观。任何对于希望真实的东西,对于三重苦难的其他两个部分同样也是真实的,因此,信仰和爱也是不能随意命令和调遣的。 在欧洲人看来,美国文化的一个特征是,它一再指挥和命令人们“快乐”。但是,快乐是不能强求的;它必须是自然产生的。人必须有“快乐”的理由。人们一旦发现了理由就会自动地快乐起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并不是追求快乐,而是通过实现内在的且隐藏于一种既定情境中的潜在意义,来寻求快乐的理由。 对于理由的需求同样存在于人所特有的另一现象——“欢笑”之中。如果你希望某人发出笑声,你必须给他提供一个理由。例如,你必须给他讲一个笑话。否则,你就不能通过催促他让他真的笑起来,或者让他要求自已笑起来。当人们催促照相机镜头前的人说“茄子”时,结果人们在完成的照片上只能看到他们虚假的笑容。 这样一种行为模式在意义疗法中被称做是“过度意向”。它在与性有关的神经症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患者越是不能忘我地献身,而是直接寻求性兴奋即性交快乐,他对于性交快乐的追求就越是弄巧成拙。实际_卜,被称做是“快乐原则”的东西只不过是快乐的破坏者。 个体寻求意义的努力一旦获得了成功,不仅能够给他带来快乐,而且还能使他获得应对痛苦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寻求意义的努力遭到了失败,又会发生什么结果呢?它可能导致一种致命的后果。例如,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在诸如战俘营或集中营这些极端场所有时可能发生的事情。首先,一些美国士兵曾经告诉我一种他们称之为“放弃一切”的行为模式。在集中营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行为模式。在早晨五点,拒绝起床干活,留在棚屋里,躺在沾着粪便的草垫上。没有任何事情——包括警告和威胁——能够使他改变主意。然后发生了一些很典型的事情∶他从口袋深处掏出一支他隐藏很久的香烟并开始抽起来。在那一刻,我们知道,在大约48小时以后我们将看着他慢慢死去。意义的意志己经消沉,结果他对于短暂快乐的追求也消散了。 这难道不能使我们想起另外一种我们日复一日所面对的类似情况吗?我想起了那些年轻人,他们分布于世界各地,自称是“没有未来”的一代。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一支香烟,他们所追求的实际上是毒品。 实际上,吸毒只是一种更为常见的群体现象,它是一种由于对我们的存在需求的挫折而产生的无意义的感觉,并转而成为工业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今天,并非只有意义疗法指出无意义的感觉在神经症的病因学中 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正如艾尔文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所指出的∶“在精神科门诊连续治疗的40名患者中,12名〔30%〕患者的问题与意义有关。”在巴罗奥托以东几千英里外的情况也只有1%的差异;最近的相关数据表明,在维也纳,常见抱怨中的29%是他们生活的意义正在消失。 至于无意义感的形成原因,人们可能说,即使是在简约化的风格中,人们也是拥有足够的生活用品,但却缺少生活的目标,他们拥有谋生手段但缺乏意义。当然,一些人甚至连谋生手段都没有,我特别想到了现在失业的大众。50年前,我发表了一篇致力于研究一种发生于年轻病人的特殊的抑郁症的文章,这种病我称之为“失业神经症”。文章指出这一神经症产生于双重的错误认同∶没有工作就等于没有用处,没有用处就等于生活没有意义。结果,每当我成功地说服患者自愿参加青年组织、成人教育、公共图书馆和诸如此类的组织时——换言之,每当他们用一些没有报酬但有意义的活动充实了他们大蛋的空闲时间时—他们的抑郁消失了,尽管他们的经济状态没有改变,他们饥饿依旧。事实上,人并不仅仅依靠福利存活。 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引起的失业神经症同时存在的还有另外几种可以追溯到精神动力学的或生物化学的状况的抑郁。根据它们可能是哪种情况,相应地,分别采用心理疗法和药物疗法。然而,就无意义感而言,我们不应忽视和忘记,它本身并不只是一个病理学问题;我不想说他是神经症的迹象和症状,相反,我认为它是一个人的人性的证明。但是,尽管它不是由任何病理学的东西所造成的,它还是可能产生病理学上的反应;换言之,它是一种潜在的病。在年轻一代中集体的神经症症状普遍存在着∶这一神经症有三种表现——抑郁、攻击和成瘾——大量证据可以归结到意义疗法所称作的“存在的虚空”,一种空虚的和无意义的感觉。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抑郁病例都可追溯到无意义的感觉,自杀——有时它是由抑郁导致的——也不总是产生于存在的虚空。但是,即使并非每一件自杀案例都是由于无意义的感觉而产生的,如果他意识到了一些值得为之生活的意义和目标,个体对待生活的动力将战胜自杀的冲动。因此,如果一种强烈的意义倾向在防止自杀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对存在自杀危险的案例,干预性因素又是什么呢?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我在奥地利最大的国立医院工作了四年时间。在那里,我负责管理重度抑郁病人的大病房——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在试图自杀后被收人院的。我曾经计算过,在这四年中我至少诊治过12,000个病人。在工作中,我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且每当我遇见具有自杀倾向的人时,我仍然会利用这些经验。我常常向这类病人说,以前有患者一再告诉我,自杀没有成功,他们是多么的幸福。他们告诉我,几周、几个月、几年之后,他们的难题确实有了解决方法,他们的问题有了答案,他们的生活有了意义。 “即使在一千个病例中只有一例发生了这一积极转变,”我继续解释道,“谁能说这种转变或早或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呢?但是,首先你必须活着去看它发生的那一天。所以,为了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你必须活下来,并且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能放弃生存的责任。” 关于群体神经症状的第二个方面——攻击行为——让我来引用一个曾经由卡罗琳·伍德谢里夫作过的实验。她成功地建立起了童子军小组之间的相互攻击模型,并且注意到,只有当这些年轻人致力于集体性目标——如把往营地运送食品的马车从泥潭中拉出来这一共同任务时——攻击行为才会消失。此时,他们不仅没有相互攻击,反面为了必须实现的意义而立刻联合了起来。 至于第三个问题——成瘾,我想起了安奈玛丽的发现。她注意到,正如试验和数据统计所显示的,她所研究的90%的酗酒者都遭受着一种极度无意义感的折磨。在斯坦利对吸毒者所做的研究中,100%的人相信“一切都看起来毫无意义。” 现在让我们转向意义问题本身。首先我想说明的是,意义治疗者关注存在于人的一生中必须独自面对的场合中的固有的潜在意义。因此,在这里我将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生活意义进行详细的阐述,尽管我不否认确实存在这样一种长期的意义。引用一个比喻,想象一场电影∶它是由成千上万的单个画面所组成的,每幅画面都表示一个意义,然而只有当最后一幅画面放映后,我们才能理解整场电影的意义。然面,如果我们不首先理解电影各个组成部分、每一单个画面的意义,我们就不能理解整部电影。生活不也如此吗?生活的最终意义,不也是在它的结束,在死亡之前,才表现出来吗?这一最终的意义难道不也是取决于每一独恃情境的潜在意义是否得到最好的实现吗? 从意义疗法角度来看,意义和它的观念是完全现实的,面不是漂浮于空中或收藏于象牙塔中。我将意义的认知定位于彪勒的“阿哈”经历和马克斯,惠太海默的“完形”概念的中间地带,此处的意义是某一具体场合的个人意义。意义的概念不同于经典的“完形”概念,因为后者意味着一个“人物”在“一个地方”的突然领悟。而在我看来,意义的概念更特别地针对看在现实的背景下意识到某种可能性,或者用简洁的语言来表述,意识到在某一特定情境下能够做什么。 那么一个人是如何发现意义的呢?正如查洛恃,彪勒指出的∶“我们所能够做的,是研究那些似乎发现了关于人类生活本质问题答案的人们的生活。”然而,除了这样一种传记性的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运用生物学的方法。意义疗法把良心看做是一种敦促者,如果需要的话,它可以指示我们在某一既定的生活情境运动的方向。为了完成这样一种任务,良心必须作为一把量尺用于一个人所面对的场合,并且,这一场合必须按照一套标准、一种价值观的等级结构来加以评估。然而,这些价值观不能被我们在良心的层次采纳和接受—价值观是我们自己的。它们构成了我们人类进化的道路;它们建立在我们的生物学的过去,并植根于我们的生物学的最深处。康拉德·洛伦兹在提出他的生物学优先概念时,可能也想到了相同的问题。并且当我们两人最近就我们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生物性基础的观点进行讨论时,他热情地表述了他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存在着一种预先反应性价值论的自我理解,我们就可以假定,它最终是深藏于我们的生物性遗产之中。 正如意义疗法所指出的,存在着人获得生活意义的三条大道。第一条是,通过创造一件作品或做一件实事。第二条是通过经历某些事或遇到某些人;换言之,意义不仅可以在工作中发现而且可以在爱中发现。在这一背景下艾迪斯坚持认为,意义疗法的“经历与成功同样有价值的观念是有治疗作用的,因为它补充了我们对于以内部世界经验为代价而获得外部世界成就的单方面的强调”。然而。最重要的是通向生活意义的第三条道路∶甚至某一绝望场合的无助受难者,在面对他不能改变的命运时,也可能超越他自身,超越式地成长,由此来改变自己。他可能将一个人的悲剧转变成为胜利。还是艾迪斯在前面所提到的,曾经表达希望意义疗法“可能帮助对抗当前美国文化中的某些不健康趋势,在这里不能治疗的受难者几乎没有机会为他的受难而自豪,不能认识到它使人高尚而非堕落”以至于“他不仅不高兴,而且他还因不高兴而感到羞耻”。 在25年中我一直管理着一家综合性医院的神经科,见证了我的病人将他们的困境转化为人类成就的能力。除了这些实际的经历之外,我还获得了一个人可以在受难中发现意义的可能性的实证性证据。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对许多越南战争的战俘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表示,尽管他们被囚禁得异乎寻常的痛苦,受尽了精神折磨、疾病困扰、营养不良和孤独寂寞之苦,但还是在囚禁经历中发现了自我成长的经验”。 但是,支持“悲剧乐观主义”的最有力的证据在拉丁文中被称做“偏见式论证”。杰里龙就是正如在意义疗法中所称做的“人的精神挑战性力量”的生动证据。“杰里龙自三年前的一次车祸以来因颈部骨折而一直瘫痪。当车祸发生时他才17岁。现在杰里龙可以用嘴咬着棍子打字。他通过特殊电话装置参加了社区大学两门课程的学习。对讲电话装置使得杰里龙既可以听,也可以参与课堂讨论。他还用业余时间去阅读、看电视和写作。”在他寄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我的生活充满了意义和目的。我在决定性的那一天所采取的态度成了我生活的信条∶我的颈部折断了,但我的人没有折断。我现在开始了大学里我的第一门心理学课程的学习。我相信,我的残疾只会加强我帮助其他人的能力。我知道假如没有受难,我取得现在的成长是不可能的。” 难道这就是说,受难是发现意义必不可少的条件吗?当然不是。我只是相信,尽管有时受难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仍能从中获得生活的意义。如果它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有意义的事就是要去除这一原因,因为不必要的受难是受虐狂而非英雄壮举。另一方而,如果一个人不能改变造成他受难的环境,那么,他仍能够选择他的态度。杰里龙无法选择是否折断他的颈部,但他确实决定了不让发生于他身上的事折断自己。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首先应做的是创造性地改变造成我们受难的环境。但是,在需要的情况下,如果具有“受难的技艺”,那就是有优势的。实证性的证据表明,百姓也是同样的见解。奥地利民意调查者最近报道,许多受访者认为具有最高威望的人既不是伟大的艺术家也不是伟大的科学家,既不是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是伟大的体育明星,而是那些经历了巨大苦难但仍然高昂着头的人。 现在转向悲剧三组合的第二个方面——罪感,我将告别我非常着迷的神学概念。在我看来,只要不能全面地探索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因素,在最终分析一桩罪行时就不能理解它。完全地解释一个人的犯罪将等同于解释他或她的罪感,不把他或她看成是一个自由的、负责任的人,而是看成一个有待于修理的机器。甚至罪犯本人也厌恶这一态度,更喜欢对他们的行为负责。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于在伊利诺伊州监狱服刑的罪犯的信,在信中,他悲叹,“罪犯们从来没有机会解释自己。他必须在各种已经给定的借口中选择。社会应当受到谴责,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指责被置于受害者身上。”而且当我在圣昆丁向囚徒们发表讲话时,我告诉他们,“你们是像我一样的人,正因如此,你们是自由地实施犯罪,成为有罪的人。然而现在,你们应通过超越它,通过超越自己,通过变得更好来克服罪感。”他们感到被理解了。并且,我收到了来自前囚徒的一本笔记,说他已经“与以前的重罪犯建立了一个意义治疗小组。我们是27个强壮的获得新生活的人,我们都是原来那个小组的成员。只有一个回去了——而他现在也自由了。” 至于集体性犯罪的概念,我个人认为,让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的行为或集体的行为负责是不合理的。自二战结束以来,我一直不知疲劳地公开反对集体性犯罪的概念。然而,有时使人们脱离他们的迷信需要许多教育的技巧。一位美国妇女曾经当面向我提出指责,“你怎么还用德语——阿道夫·希特勒的语言——撰写你的一些著作?”作为回答,我问她的厨房里是否有刀,当她回答有时,我做出沮丧和惊恐的动作并惊叫道,“你怎么能够在许多杀手用刀谋杀了许多受害者之后,还使用刀呢?”由此,她不再反对我用德语撰写著作。 悲剧性三组合的第三个方面与死亡有关,但它与生命也有关系。因为在任何时候,构成生命的每一时刻都在走向死亡,并且这一时刻从不重复发生。然而,正是这一短暂性提醒我们尽力过好生命的每一刻。它当然是,并因面成为我的警句∶“尽情地享受生活,好像你已经获得再生;面不要像你初次那样,错误地来做今天的事!” 实际上。恰当地做事的机会,实现一种意义的潜在可能性,受到了我们生命的不可逆转性的影响。但是潜在可能性本身也受到这样的影响。因为一旦我们使用了一次机会,实现了一种潜在的意义,我们这样做了一次也就是全部了。我们把它放入了过去,在那里它被安全地储藏起来。在过去,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逆转地失去,相反地,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可逆转地储存和珍藏。当然,人们往往只看见田野里的残株而忽视了过去的丰厚收获,他们带来了生命的收获∶完成的业绩,爱过和被爱,最后是他们带着勇气和尊严经过的苦难。 从这一点出发,人们可能知道,没有理由去怜悯老人。相反地,年轻人应该嫉妒他们。确实,老年人在将来没有了机会,没有了可能性,但是他们拥有比这更多的东西。与将来的可能性相反,他们拥有过去的事实——他们实现了的潜在可能性,他们完成了的意义,他们实现了的价值——任何人都不能从过去消除这些宝贵财富。 在看待发现受难中的意义的可能性时,生命的意义是无条件的存在,至少是潜在的。这一无条件的意义是与每个人无条件的价值观相对应的。正是它保证了人的尊严的不可消除性。正如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具有潜在的意义一样,甚至那些最悲惨的人,每个人的价值也永远与他或她在一起,因为它是以人在过去已经实现的价值为基础的,并且不是发生于现在可能不再保持的有用性上。 更详细地说,这一有用性常常是根据对于社会福利的功能来定义的。但是现今的社会的特征是成就导向的,结果是它高度崇拜成功而快乐的人,并且它尤其崇拜年轻人。它实际上忽视了其他人的价值,并且通过这样做,它模糊了在尊严方面的价值与在有用性方面有价 值之间的决定性区别。如果某人不认同这一区别,并坚持认为,个人的价值是来自于他的当前的有用性,那么,说实在的,人们应当为按照希特勒的思想实行安乐死计划辫护,否则就会产生矛盾。这就是说,“仁慈地”杀死那些失去了社会用处的人,因为其年老、不能治愈的疾病、智力低下或者有残疾的人是有道理的。 仅仅用有用性来混淆人的尊严,产生于一种概念上的混乱,它可能被追溯到传播于许多大学和许多分析性表达中的虚无主义。甚至在训练分析的背景中这样的灌输也可能发生。虚无主义并不认为,不存在任何事物,但它表明,任何都是无意义的。当他发表“有学问的意义”概念时,他是正确的。他本人提起的一位治疗者曾经说过,“乔治,你必须意识到世界是一个玩笑。没有公正,任何事物都是随机的。只有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你的一本正经有多么的傻。在宇宙中没有大的目的。仅此而已。在你作决定时没有特别的意义。” 我们不必将这一批评普遍化。原则上,培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是这样,治疗者应该看到,他们在使受训者免除虚无主义的影响,而不是向他们灌输愤世嫉俗主义,这是一种反对他们自己的虚无主义的防御机制。 意义治疗者可能遵守一些由其他心理治疗学派规定的培训和认证要求。换言之,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 与狼共舞。但是当这样做的时候,我建议,我们应当是披着狼皮的羊。没有必要对于人的基本概念和生活哲学的原则不忠实,这些概念是存在于意义疗法之中的。这样一种忠诚并不难保持。鉴于事实,正如伊丽莎白所指出的,“在心理治疗的全部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学派像意义疗法那样不墨守教条。”并且在意义疗法第一次世界大会上〔1980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我不仅赞成心理治疗的再次人性化,而且还支持我所称做的“意义疗法的去权威。”我的兴趣不在于培养只会重复“他的师傅声音”的鹦鹉,而是在于将火炬传递给“独立的、有创新的和创造性的精灵”。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断言,“让我试图将大量形形色色的人统一地暴露给饥饿。随着饥饿程度的加剧,个体差异将会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一种不安宁的、急迫的相同表情。”感谢上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不知道集中营的内情。他的主题放在了用维多利亚豪华风格设计的睡椅上而不是奥斯维辛的污秽处。在那里,“个体的差异”并没有“模糊”,而且相反地,人们变得更加不同了;人们揭去了他们白己的伪装,猪和圣徒都是这样。并且,今天你不用犹豫地使用“圣徒”一词;想一想马克西米伦神父,在奥斯维辛忍饥挨饿,并最终被注射进了石碳酸而遭到谋杀,并在1983年被封为圣徒。你可能责怪我引用了这些非常规的例子。但是,请阅读斯宾诺莎《道德论》的最后一句,所有伟大的事物就像它难以被发现一样地难以被意识到。当然你可能询问我们是否需要提到真正的“圣徒”。仅仅提到高尚的人还不够吗?确实,他们只是少数人,他们总是少数。但是在这里我看到了加入少数的挑战。由于世界处于一种糟糕的状态,除非每个人尽力去做最好的,否则所有的事情将还会变得更坏。 所以,让我们保持警惕——双重意义上的警惕∶从奥斯维辛,我们开始知道了人能够做什么。从广岛,我们开始知道了人正处于何种危险之中。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