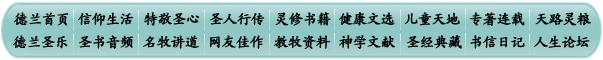第三天,米沙很遗憾地告诉我,他没能修改病历。他说我可能会去卡耶尔坎,但问题在于没人愿意去矿区,有些罪犯甚至以自残的方式防止自己被派去那里。结果,官员们对病历展开严格检查,凡是能被他们按规定划为健康工人的人都会被征用。万不得已时,我加入了一个声称知道如何制造高血压假象的团伙。我觉得,为了远离矿区而吞下肥皂或切下一个脚趾,对我的健康是不值得的,但我愿意尝试一下。
就在体检前,我们去澡堂洗了个热水澡,水温恰到我们可以忍受的热度。其中的诀窍就是拼命屏住呼吸,直到你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仿佛随时都会爆裂。然后立刻冲向医疗中心。如果你运气好到能马上见到医生,你的血压读数就会高得很危险。这样一来,你将被免去几天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医生会在你的病历上写下“高血压” 。有的人侥幸逃脱了征用,但我从医生那里拿到的是降血压的处方以及派往卡耶尔坎的通知。
据说我们之中大约有400人被选入了矿区。我们领取了毡靴以外的冬装,在五号营外面接受检查,然后穿过城市来到了铁路调车场。那一年在十月就已经冷得要命了,我们站在调车场内等待登上杜金卡-诺里尔斯克铁路的小型窄轨车厢,此时大风不断撕扯我们的棉袄。很多车厢里没有供暖,过于老旧,连木板都开裂和变形了。
卡耶尔坎大约位于杜金卡-诺里尔斯克铁路的三分之一路段处。小火车在刚刚下起的大雪中穿行,绕过祖布戈拉(Зуброга)——诺里尔斯克城外的一座富饶的矿山,驶入空旷的郊野。然后,列车在一个只有两三间棚屋的小岔路停靠了很久。我们在车厢里不停地原地踏步,努力使血液保持循环。最后,我们发现列车是在等人来清扫前方的路轨。大雪已经转为暴风雪,列车花了将近三小时才行进了十五里,终于抵达卡耶尔坎。
这座城镇是一座典型的矿业城镇,一切事务均以矿区为中心,火车站离矿井不到半英里。火车站本身规模很小,但庞大的铁路调车场里有十几条铁路支线,用于承载来自矿区的运煤车皮。这里和扎帕德纳亚一样,有一座朝杜金卡方向延伸了好几英里的山脉,而矿区入口就开凿于这座山脉的山坡中段。工作井基本上是水平的,而不是纵向的。卡耶尔坎的劳改营位于火车站和矿区入口之间,所以它可能距我们下车的车站不过400英尺。
我们赶紧在漫天大雪中排好队,然后急匆匆地穿过了营地大门。负责运送的警卫仅仅是把我们的证件交给营地官员,随即登上了返回诺里尔斯克的火车。我们一进营地便被分为两组。一半的人去俱乐部办理手续,其余的人去了澡堂。
检查的程序差不多用掉了一整夜时间:登记、根据工作资格分门别类,以及例行的洗浴、理发和消毒程序。不过,最花时间的是严格的体检。这里的营地官员不相信我们带来的病历。如果有人被发现有恙,那么此人就会被送回诺里尔斯克。他们不希望这里的矿区存在任何无用之人。
第一天晚上,我睡在俱乐部里,第二天才被分配到营房。在卡耶尔坎这里,新来的人并没有被立即分配到生产队,我们被转交给一个特别的主管,他将我们安置在临时营房里,在此期间我们将接受采矿理论、采矿实践以及安全规则的培训。我们还从图表上了解到矿区的整体布局。这些课程从上午九点进行到十二点,中间有十四分钟的休息时间,下午则从一点进行到三点。整个培训历时三周,培训结束后我们必须参加口试和笔试。
在这三周内,教官还带着我们进了三次矿区,每次都是在不同的班次,他向我们展示了矿区内部的实际情况,以及操作流程中的每一个步骤。当我们考试合格并签订遵守矿井安全规定的承诺书后,终于被分配到了一个生产队。当天下午,我们就从初级营房搬到了生产营房,并在次日开始工作。
即使在矿井里,空气也是非常寒冷。地面被冻得很坚硬,巨大的通风装置在井下制造出巨大的风,以防止瓦斯包的形成。因此,我们在矿井里一年四季都要穿冬装——内衣、上衣、棉袄、裤子、毡靴、围巾和头盔下的毛皮帽子。有些人喜欢在工作中穿靴子而不是毡靴,但如果穿着靴子,就必须不停地走动,不然脚会冻僵。
通常情况下,任何时间段里都有大约八个工段在主工作井之外工作。从运送我们进山的车厢下来后,我们沿斜坡走了大概四分之一英里进入工作井,井内的支撑木是用厚重的梁木搭建的。为了防止木材腐烂,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木材都经过了粉刷。为了防止暖空气从主井口进入工作区将冻结的地面融化,大约每隔150码就有一个隔板。我们很快从那座工作井进入工作区。实际上,始终有两个工作井是与煤脉平行的:一个工作井是用于将煤运到收集仓的传送带网络,另一个位于煤脉的另一侧,用于运送支撑工作井的木材。
每条煤脉上方都有一层3英尺厚的页岩,页岩的上方是砂岩。横穿煤矿脉的工作井约有90码宽,但没有一条工作井能一次深入120码以上。当工作井接近这个长度时,我们能听到顶棚上的砂岩发出枪声一般的开裂声,还有巨大的岩块相互摩擦所发出的尖啸声。在我们身后,工作井的一些支撑木会在砂岩的重量下断成两截。
随着矿井的长度不断增加,这样的噪音越来越多。沙子开始从顶棚落入矿道里。那是一个危险的征兆,生产队长会马上命令我们将设备从井里拉出来安置在侧井里。没过多久,整个顶棚就会急速崩塌,并且将空气冲出井外,如果不卧倒的话,这股冲击波会使人撞上岩壁,将他的肋骨撞碎。巨大的支撑木会像火柴棒一样折断,冲往各个方向,偶尔会在我们卧倒时撞上我们头顶的岩壁。
有时我躺在床上彻夜难眠,一想到自己被困在矿井里,顶棚从头顶塌下来,我就会瑟瑟发抖。随着矿井日益变长,一些工人出现了严重的神经性疾病。顶棚塌下后,我们会沿矿脉绕行15码,在两个辅助井之间切开一个新的工作面,然后重新开始工作。我们会一次深入矿脉中约10或12码,将孔洞填满火药,装上雷管,然后发起爆破。
之后,我们将炸出来的煤块击碎,然后把它们铲进铲运机线路里,铲运机会把它们拖出来,倒在通往上方料斗的传送带上。矿井立即被直径24英寸的木料支撑起来,每根木料相距约一码半。但是,首先必须把顶棚上的页岩敲下来。否则,由于地面的解冻,页岩和砂岩之间的空间内会形成积水,如果它塌下来,可以把一个安全帽直接砸成两半。
有一天晚上,我差点就被砸死了。那时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切口,为的是给铲运机的绞车预留空间。我注意到顶棚上的板岩没有得到很好的剥离,我对此不放心,于是向工头报告了这一情况。“别担心,”他说,娴熟地观察顶棚,“明天之前不会出事的。”我和另一人一起铲出一堆板岩和煤,我敢肯定,每当我看着那块顶棚,裂缝越来越大,沙粒不断落下。我紧张起来,又提醒了一次工头。他检查了一遍,认为已经够安全了。他告诉我,我们必须完成切割并把铲运机安置好,因为上白班的工作人员即将开始爆破。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清除顶棚上的板岩。
我们还是很紧张,为了在工作时尽可能远离顶棚的危险,我和搭档拿起了长柄铁铲。我们都知道板岩掉下来会发生什么事。那是糟糕的一夜,直到白班的工作人员于7点45分报到上班。我很高兴能够离开,我向刚来的工人和大队长指出了有问题的顶棚。“你们最好赶快搬一些木材下去!” 我说。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始工作,整个顶棚就塌了。有一个中国人被压倒了,他的脊柱断成了两截。他存活的时间还算长,其他人得以将他送往矿区医院。
尽管工作很危险,但营地本身的条件几乎比我到过的任何营地都好。诺里尔斯克周边的发电厂和熔炉亟需这些煤矿的煤炭, 这些煤炭还会从杜金卡出口到国外,换取农业机械和工业设备。因此,官员希望囚犯能够有效地工作, 所以他们尽力让生活能过得下去。
营房内部的环境很好,床铺干净舒适,食物也不错。除了食堂的普通食物配给外,在大门边上还有一间我们和自由工人共用的餐厅,我们可以在那里买一顿餐食。这样的一餐包含肉、麦粥、烙饼和甜点,还有蛋羹或苹果干,有时甚至还有西梅干。这样的一餐很贵,但十分划算。你还可以在这里的餐厅和营地商店买到糖果、饼干、香烟和其他奢侈品。
无论是囚犯还是自由人,矿工领取的工资大体相同——每月约3000至5000卢布(300至500美元)。但政府会从囚犯的工资中克扣一定比例,劳改营又会扣除一定比例的食宿费,所以我们的实际工资是每月100至300卢布(10至30美元)。有了这些钱,我们可以购买食物和其他奢侈品,还能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农民那里买到洋葱和大蒜——这些农民获准向矿工出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
每个人都在尽可能购买这些东西。它们既是维生素的来源,也是坏血病的预防用药,这里的坏血病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更为泛滥。我注意到它集中在我的手臂和腿部,那些部位会出现蓝色斑点,而且变得像熨斗一样沉重,身体是如此沉重,以至于我连走路都很费劲。尽管营地的条件不错,但卡耶尔汗的囚犯总是疲惫不堪,脸色苍白,从来休息不够,永远累得要命。
我们还可以从那些在矿区与我们密切合作的自由工人那里获得额外食物。有时他们会直接给囚犯中的朋友送礼物,而且只要我们给钱,他们就乐意到城里买我们所要的东西。因此,营地大门的检查在一个班次结束后往往比平时更严格。警卫会让生产队中的每个人都在营门前脱光衣服,看我们是否走私肉类或黄油——伏特加尤其受到注意。

一间劳改营中的面包房
在一次搜身中,一个来自立陶宛的年轻警卫在我的衣服里发现了一个写有祷文的小本子,上面用拉丁文写着整场弥撒的事项。他本想没收它,但我求他不要这么做。因为他是立陶宛人,我向他坦白了自己的司铎身份,告诉他这是弥撒的祷文,我说:“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他悄悄把小本子递回我手上,然后放我通行。
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在意我在这个劳改营里所做的司铎工作。我有一两次受到了审讯员对“颠覆性活动”的警告,但我每天都会做弥撒并分发圣体,每周都与几伙囚犯谈话,为他们讲道、开讨论会,甚至还做了一些避静。除我之外,在卡耶尔坎劳改营还有三位司铎。
其中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卡斯帕神父,他曾在杜金卡和四号营同我住在一起。我一到这里,他就前来欢迎我并安排我去做弥撒。还有一个立陶宛人——亨利神父,他又高又瘦,头上有几块秃了,蓄有灰色的髭须和山羊胡子,他被捕前曾是一名修道士。亨利不在矿区工作,而是在一个营地里当勤务员,因此,他的营地成为生产队在矿区时最适合做弥撒的地方。他还收到了很多立陶宛人送来的包裹,这意味着他的营房也是一个蹭饭的去处。
最后一位是尼古拉神父,他是一个高大的乌克兰人,体格健壮,声音轻柔。他也曾是一名修道士,不过属于东仪教会。他在营地里的乌克兰人中很受欢迎,他们愿意为他赴汤蹈火。事实上,他们中最出色的是一个名叫德米特里耶夫的乌克兰人,他是一个瘦小的黑发男子,长着一个尖鼻子和一捋山羊胡。德米特里耶夫在囚犯中人脉最广,是一名了不起的平信徒传道员。
由于宽松的政策,这里的囚犯感到自由多了。令人惊讶的是,由于外部的迫害没有了,现在有很多人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是“被容忍的”或者至少是被姑息纵容的。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我们甚至在劳改营举办了聚餐庆典。虽然警卫们知道这些事,但他们假装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会在下午五点左右进行晚间检查,不过仅仅是告诉囚犯不要太过喧哗。
每个宗教团体都会在这些节日里分到一个单独的营房。一间营房是东仪天主教徒的,另一间是东正教徒的,第三间则是浸信会教徒的,以此类推。由于囚犯的精神,我们甚至可以安排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不用在宗教节日工作,作为报答,他们会在官方节日里替不信教的人上工。这些人在为庆典布置营地时,表现出了惊人的聪明才智。他们用床单遮盖营房里的长桌,用种种办法从营地餐厅弄来碟子、银器和酒杯,还准备了用碗盛装的各种民族菜肴。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拿来了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有腊肠、通心粉、肉类、黄油和其他美味佳肴。
在这些日子里,每位神父都在不同的营房里做弥撒。在卡耶尔坎,我近十五年来首次为整座营地的人做了一场“公开”弥撒,他们当时还唱了起来!难怪警卫要告诫他们保持安静。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参加了圣体圣事,之后,我在弥撒后的聚餐上做了一次很长的讲道。
用餐前,我们给食品降福,用俄语做起了庄严的感恩祈祷,然后用圣水给营房降福。随后,我们的聚餐开始了。威士忌在营地是被严令禁止的,但是在这种场合,威士忌在餐桌上随处可见。就连警卫也会进来喝上一杯,吃上一口节日食品,他们再次警告人们保持安静,然后就出去了。他们从来不向官员报告这些事。
在卡耶尔坎这里,许多囚犯的刑期即将结束。差不多每天都有人从劳改营被释放。为了替补那些离开的人,不断有新的囚犯被送过来,你可以从疲惫的脚步、手脚活动的方式以及严重的坏血病认出人群中的老囚犯。下班后,很多人会搭乘运煤的传送带升到矿井上方,而不是徒步返回,这本是被严格禁止的。有一天,我在搭乘传送带的时候睡着了,结果落到了煤仓上面,煤块如雨点般砸在我身上。所幸我没有被砸死,而且很快就逃了出来。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如今,最悲惨的案例就是那些本来过几天就会获释,却在矿井中死去的人。所有人都在谈论和思考这个问题,有些人光是一想到这个问题就几乎精神崩溃,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下矿井,他们害怕的是,自己好不容易活了这么多年,却在到达终点前死去。这种紧张情绪并没有减少事故,事实上,事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有一天,七人在爆破过程中的闪爆中死亡。这一伙特殊的工作人员当时正在爆破一个新切口,而且是在通风不良的密闭空间里工作。在这种环境中,你能感觉到空气中刺鼻和闪亮的煤尘。实际上,他们当时身处工作区外一个本应是安全的矿井中,却被爆破后的闪爆灼烧而死。

劳改营死者的骸骨
我在听说这件事后不寒而栗,因为我也在某天遇到了这样的事。当时我们完成了一个新切口,准备进行爆破,所以我被派到安全井上方,以防止有人进入该区域。不知怎么的,我在黑暗中迷路了,站在工作井新切口的正对面。爆炸声突然响起,我被炸飞到井道的中段——我的身体被抛了起来,撞上了矿井顶部的一根木料。我昏迷了两个多小时,所幸没有被炸死或炸残。
到了1955年的春天,一个名叫雅诺斯的年轻立陶宛医生在卡耶尔汗的医疗中心告诉我,如果我还想活下来,就必须离开矿区。我对他说,我的刑期只剩三个多月了,或许我能够坚持到最后。他告诉我,除非我离开矿区,否则不可能活下去。雅诺斯是个中等身材的小伙子,长有一头栗色的头发和一副红润的脸颊,留着一点小胡子。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但他了解自己的责任,决意为我当前的状况做点什么。
在这里,工作分配表每三个月换一次,而不像其他营地那样每月更换一次。春季工作分配表到期之后,雅诺斯在我的病历卡上写下一串长长的病史,其中包含了各式各样的疾病——并非所有这些疾病都是我曾得过的。不过毫无疑问,我的身体已经明显变得虚弱了。雅诺斯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下周的主日弥撒时对我说,下周的勤务簿上应该不会有我的名字。但在官员在营地宣读名册时,我还是被点名分配到了矿区。
那天早上我遇见了雅诺斯,他很生气。他叫我当天先去上班,但他会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那天早上我们正要排队离开营地时,他跑来追上我,然后叫我回营地。接下来,他就去医务室把我的名字记在了当天的病人名单上。
上午10点左右,雅诺斯冲进营地医生的办公室,那位医生当天上午正与镇上的三名自由人女医生开会。雅诺斯挥舞着我的病历卡,质问主任为什么没有被免去我在矿区的职务。他喊道:“如果他死了,我就举报你! 我不会再负责任了。正是我写了这张病历卡,而且建议免去他的职务。如果他死在矿区,我就把所有人都举报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病历卡扔上桌子,随即走出房间。
那位主任医师连忙追到走廊里把他叫回来。他被吓坏了。尽管医生怀有世上最善良的意愿,但他们知道在劳改营根本无法对病人尽职尽责,因此,他们不希望市委会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调查。主任医师直接陪雅诺斯找到工头,将我的名字列入了即将更换的名单中。
那天,雅诺斯在医疗中心办完事后找到我,说我已经正式脱离矿区了。我很高兴,这个消息让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坚强,更有活力了,我对雅诺斯的感激之情再深也不为过。
第二天,我被正式分配到一个在马场工作的生产队。生产队长让我独自一人上夜班,因为这是一份“轻”工作,我要从晚上六点一直干到早上六点。我的工作就是打扫卫生,给马匹添水,打理畜栏,晚上清理马厩并给马喂食,到了早上再重复这一套工作。尽管工作时间很长,但其实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我是自己的管理员,可以小憩一很长时间,由于远离矿区的瓦斯和灰尘,我的健康状况几乎立刻开始好转。
我们的马厩里只有八匹马和六个骑手。这些马被专门用来在冬天拉雪橇,将物资——炸药、机械、工具和木材运往矿区,或者卸下火车运来的物资和食品。马匹年轻而好动,它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每天都要工作十二小时以上。
在流放地运送物资的马队
骑手们也很年轻,他们大多是农家子弟。起初,我有点害怕马,他们教我如何驾驭马匹、如何给它们套上马具以及如何清洗它们。然而,有一匹名叫瓦什卡的小蒙古马却让我几乎束手无策。它是一匹健壮的白色小种马,身上有灰白的斑点,它的畜栏是马匹中最大的,因为他像骡子一样总是乱踢,而且还咬人。他额头两侧的眼睛总是闪着红光,我确信这匹马疯了。最初的两个晚上,我连喂饲料时都不敢靠近它。只要我一踏进它的畜栏入口,它就会咆哮起来,恶狠狠地踢踏墙壁和大门。
就这样过了几天,瓦什卡的骑手在一天晚上对说我:“老瓦什卡这些天有点不对劲。他似乎不像往常一样有劲,我根本没法让它拉车。” “好吧,我承认,”我说,“我没法进去喂他。每次我想进去,它都差点把我的脑袋踢飞。我可不想在刑期只剩两个多月的时候被一匹疯马踢死。”
我以为那位骑手会生气,可他却开心地笑了起来。然后,他告诉我,他会教我如何对付瓦什卡。他大步走到畜栏前,大声喊起马的名字,跟个赶骡人似的骂骂咧咧起来。瓦什卡一脸惊恐的样子,他没有踢踏或用鼻子喷气,而是小步后退到畜栏的角落里,眼睛闪着光。“看,这再容易不过了。”骑手说,“你得先下手为强,比他更凶更狠。来,试试吧!”
我并不太喜欢这个主意,但我用一只手拿着一桶燕麦,朝瓦什卡的畜栏走去。我开始大吼大叫,同时挥舞起那只空闲的手,拼命喊出一切自己能想到的东西,并把老瓦什卡的名字插在每一句话的中间。这招果然奏效了,瓦什卡露出一副怯生生的表情,红着眼睛缩在畜栏的一个角落里。我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把燕麦倒进食槽里,随后走出畜栏,关上身后的门。自那以后,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真正的专家,与瓦什卡打交道时再也没出麻烦了。
大约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我被叫去劳改营办公室,并在那里得知我将在10天后获释。他们在先前检查我的记录时,发现根据新规定,我的刑期因额外劳动而减少了三个月,因此我实际上只用服十四年零九个月的刑。于是,在我的空闲时间里,我开始了又一轮体检以及与各获释事项相关的繁琐文书工作。
在我离开前的那天晚上举办了一个欢送会。这可以算是卡耶尔坎的传统,因为已经有很多人从这里离开了。人们发起募捐,每个人都想办法帮了点忙,有人给了3卢布,有的人给了5卢布,还有人偷出一条新棉裤和外套送给我。那一夜,我们去营地大门附近的自由食堂占了几张桌子,接着聊了很长时间。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建议,他们告诉我要去哪里,去看谁,去哪里寻找事先出狱的老朋友。作为回报,我承诺如果能在附近见到他们的家人,就会尽可能去拜访他们。他们给了我一些便条,上面写有出狱的预计日期,并且让我转交。
次日清晨——1955年4月22日,我醒了。我想自己在当晚完全没有睡着,单纯是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在15年后获得自由了。大约九点时,工头来叫我,然后把我带到克格勃办公室。我在那里待了约两小时,签文件、填表格。我以为可能会有麻烦或是又一场审讯,但一切无非是例行公事。他们公事公办,对我的关注度不比对其他囚犯的关注度更高。
尽管如此,我依旧十分紧张和焦虑。我穿着一双旧毡靴、一件新棉袄和一条新裤子,还戴了一顶带有棉护耳的帽子。我所有的私人物品都在几年前遗失了。在上午的文件办理程序中,其中一名克格勃的人交给我一封信和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是索尼娅的,她是我从前在阿伯丁时的教友之一。她在1949年给我寄了照片,而我今天才拿到它们。我把两张照片和我口袋里的50卢布(5美元)塞到一起,这50卢布是我在世上的全部财产,其中包含我剩下的工资以及昨夜聚会上收到的筹款。
我一直在等候克格勃的指示,但他们只是开始事无巨细地对我的新身份做出说明:当你离开劳改营时,你不会得到护照,而是会得到一份所谓的“获释文件”,这是一份说明你已经服完刑期的证件,还有一份用于证明公民身份的报告书。一个囚犯有可能是完全获释并得到改造,也可能是不完全获释,比如我这种情况。作为一名被定罪的间谍,我得到了一份所谓的“限制性证件”(приложение паспорта)。
由于限制性证件,你能生活的场所是受限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你能赚多少钱也是受到限制的。比如,当时有一项极为丰厚的极地奖金,名为“极地津贴”(заполярье),特别发给那些在西伯利亚北极地区工作的人。那是政府为了吸引工人来这个严寒的边疆地区而出台的奖励政策。一个人在这里工作的时间越长,奖金就越多,假如他在西伯利亚工作5年,就可以获得两倍于工资的奖金。
由于受限制的公民身份,我没有资格享受这份极地奖金。我也不能住在自己我想住的地方。我未获准居住在任何“政权城市”,即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塔什干这样的大城市,也不能住在任何边境城市,根据他们的预测,我可以从那些城市出国。我只有在得到政府的明确许可后才能访问这些城市,而且访问时间不能超过三天。另外,由于限制性证件,我在任何城市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警察报告,并且登记我在那里的住所。

保存于苏联档案中的齐赛克神父文件
官员对我说明了所有的事项,然后检查了我的劳改营文件——那大概是第一百次检查了,他们叫我带着获释文件去诺里尔斯克的警察那里报到。在那里我将得到一套正式的身份证件。1点半,全部事项都完成了,我最后一次走出劳改营大门。习惯性地走了大约十五步后,我停下脚步等候警卫。囚犯和警卫们都望着我笑了起来——被释放的囚犯中十有八九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已经完全习惯于囚犯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不知道该如何像自由人一样走路。我的双臂垂在两旁而不是折在背后,我感觉十分奇怪。我盯着营地看了很久,仿佛是要阻止自己离开,然后将手插进口袋,朝卡耶尔坎方向走去。火车站内停了一列火车,我登上车厢,没有人注意到我。所有的一切都令我难以置信,仿佛一部电影的画面在我眼前陆续展开,仿佛这是一场随时都会醒来的梦。
列车员是一名女性,她查收了我的车费。我原以为她会问我一些问题,或者找我麻烦,但她只是礼貌地微笑着。我坐在座位上看向窗外,差点就哭了出来——我被当作自由人对待了。我一直在等候什么事情的发生——或许有人大声喊叫,或许有人阻拦火车,又或是有人用手对我指指点点——但什么也没发生。我坐回原位,望着山脉与矿区,望着从料斗里涌出的煤与劳改营——接着,火车启动了,我踏上了前往诺里尔斯克的旅途。
(第三章《诺里尔斯克的劳改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