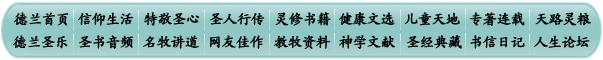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个学会祈祷的时刻。对我来说,这个时刻是在1945年2月13日星期二晚上九点过后的德国德累斯顿,在那场使这座美丽的城市化为废墟的毁灭性空袭中出现的。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跪在地上真诚地向上帝祈祷。
我,一个美国人,怎么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身在德累斯顿?我的父母出生于德国,但已归化为美国公民,他们于1938年回到祖籍国暂住。一年后,战争爆发,我们被禁锢于此地。我当时21岁,德累斯顿空袭发生时,我的父母、我的哥哥乔治和我已经在软禁中生活了近四年。我们被限制在该城市的范围之内,行动受到严格监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当我身处致命的危险之中,炸弹爆破产生的震荡使我跪倒在地,然后我才会转向上帝,求祂作我的避难所和拯救。我的父亲查尔斯·诺布尔曾是一个虔诚的人。事实上,他年轻的时候曾短暂地担任过牧师。至于我为何变成了一个仅关注世俗事物的年轻人,我无法充分地解释。
这无非是一种倒退。上帝慷慨地将物质财富赐予我们整个家庭,但我们没有回以适当的感恩。
家父于1892年出生在卡塞尔的洪堡(Homburg, Kassel province),他的父亲在那里拥有一家小型制鞋厂。他们家原本信奉路德宗,但家父11岁时,在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努力下,我的祖父皈依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新的信仰对他来说意味着切实的牺牲。虽然德国的工厂普遍推行六日工作制,但我祖父从此不在星期六经营他的工厂,而且在冬季不得不在星期五下午关门,因为在隆冬时节,太阳是在下午3点半落山的,而基督复临派的安息日纪念活动在日落前一小时开始。
新的信仰也使这个家庭与德皇威廉二世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发生了冲突。1913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我的父亲被征入德国军队。作为一个依良心拒服兵役者,他拒绝在星期六扛枪或执行任何军事任务。他因违抗命令而被关了禁闭。在五个月的时间里,他通过祈祷使自己坚强起来,经受住了变本加厉的虐待和惩罚。后来有一天,一件奇事救他脱离了困境。
军队监察长要来检查新兵,上尉命令全体人员,当然包括我的父亲,穿上他们的军装,在阅兵场上列队。家父年轻时受过伤,脖子朝一边略微偏斜,他的头抬起时总会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倾斜。
当众人都戴着高耸的普鲁士头盔列队时,家父的头导致队列中出现了不整齐的情况。将军干脆利落地命令他把头摆正。当家父回答说自己因旧伤而不能从命时,将军下令立即将他送到医院,看看医生是否能做些什么。外科医生回答说,这种伤是永久性的,团里的上校以此为由让家父因病退伍。
在几个月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作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西部前线工作,为伤员和濒死的人带去援助和尽可能的安慰。虽然常常暴露于枪林弹雨之下,但他没有受过伤。他后来回想起来,或许这段经历构成了我们日后的一部分麻烦。上帝赐予我们的福气如此之多,导致我们将这些福气视作理所当然的。
战后,父亲去了一所圣经学校就读。基督复临派的青年团体经常到那里开会。在一次聚会上,他遇到了一位迷人的姑娘,希尔德加德·格林,她的家人也是基督复临派的成员,不久,这对男女结为夫妇。最终,德国的基督复临派因教义问题而分裂,家父成为被称作“改革派基督复临会”的一个小宗派的牧师。他先去柏林,然后去了瑞士,最后被派往美国,在底特律牧养德国移民。1923年9月4日我出生时,他正在那里的一个街角地块上主持福音聚会。
基督复临运动的创始人埃伦·怀特(Ellen Gould White)的著作没有多少德文版本。当我的父亲开始了解英语,并更加广泛地涉猎时,他开始怀疑自己所宣扬的一些教义的智慧。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最终不得不认识到,当他自己对许多教义产生严重怀疑时,就无法再敦促他人加入改革派基督复临会。因此,他辞去了牧师的职务,之后也没有加入其他教会。我们家随波逐流,很少参加教会的礼拜,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宗教的关心越来越少。
父亲仍然相信复临派所倡导的素食主义具有健康价值,经营起小规模的健康食品生意。1929年,底特律的斯图兹摄影公司(Stutz Photo Service)——家母曾担任该公司的摄影专家,其持有者在一次车祸中去世,这家公司被挂牌出售,这给了我们进入摄影领域的契机。我的父母筹措了他们所能借到的一切,收购了这家公司。1929年正值股市大崩盘的前夕,对创办新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个有利的时机,但我们的好运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持续下去。
我的父亲在开始创业时没有任何先入之见,在一些新型自动照片冲洗设备上投入大量资金。多亏了这种自动化工艺,我们能以比我们的竞争对手更低廉的价格处理业余摄影师的照片,而在那些日子里,受到经济萧条冲击的底特律人正在寻找各种方法来节省每一分钱,尤其是涉及非必需品的领域,比如兴趣爱好。到1934年,我们有220家门店提供冲洗和售后服务,我们的工厂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工厂之一。
然而,经济上的成功是在不断牺牲生活中其他价值的情况下取得的。上主使我们兴旺,但我们却忘记了回以感恩。随着我和哥哥长大,曾经作为家庭生活之一部分的每日读经逐渐消失了。父亲每天只在晚餐时做一次感恩祈祷。有时我和哥哥轮流在其他用餐时间做感恩祈祷,但仅仅是习惯使然,对我们不具有真正的意义。当我仍只是个孩童时,我家就完全不再去教堂了。
1935年,第一次有人警告我们,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积累物质财富是不好的。当时,父亲患上了重病。他被诊断患有胆囊疾病。捷克斯洛伐克的卡尔斯巴德(Karlsbad),有一个著名的疗养胜地,朋友们建议家父在那里寻求帮助。他去了那里,取了当地的水,回来时身体得到了休整,病情大为改善。但很快,生意的压力使他的身体再次崩溃。他去了几次卡尔斯巴德,在某次旅行中遇到了一个为免遭纳粹迫害而逃出德国的犹太商人。尽管这位先生获得了瑞士公民身份,但他决心卖掉他拥有的一家位于德累斯顿的相机工厂,然后移民去美国。家父很清楚德国相机的价值,以及它们在美国的良好市场前景。我们在底特律获知的首个关于这桩生意的消息,就是父亲出售了我们在底特律的摄影公司,收购了德累斯顿的一家相机工厂。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他无法在底特律以缺席的形式经营这座工厂。1938年,我在八年级时退学,陪同父母到德累斯顿,以便我的父亲能把工厂事务安排妥当,然后去拜访疗养院。

图1 十五岁的约翰·诺布尔 照片摄于1938年 |
1939年,随着希特勒丧心病狂地将他的装甲部队派往波兰,风暴的阴云降落在我们头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打响,我们不得不登记为外国人,显然,我的父母作为已归化美国的德意志人,为纳粹所猜忌。不过,我们的生活仍在俯瞰城市的山顶房屋里平静而舒适地持续着。我忙于在工厂里学习和工作,以便了解它的运作情况,并且在夜校上课,学习古板的德国高中课程。
在德累斯顿,有一座无宗派的美国教堂,我的朋友们会去那里参加圣诞节和复活节等特殊节日活动。我们家却遗忘了祈祷、读经,甚至进餐时的感恩祈祷。
狂暴的逆风席卷了这个战火纷飞的世界,我们却依然没有察觉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参战,我们被软禁在屋子里,我们的相机工厂也遭到严厉的管制。父亲以他对抗德皇军国体制时所表现出的同样的冷静沉着,告诉纳粹,一旦他们要他开始生产任何战争物资,他就会身败名裂,但如果他们愿意相机通过瑞士和瑞典等中立国家销售,他会继续经营他的工厂。由于关键的工人被征召去服兵役,父亲的在场对于工厂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而纳粹也勉强同意他继续工作。但是,随着战争开始对德国不利,我们面对越来越大的敌意,父亲下定决心,我们必须要求将我们遣送回美国。
1945年1月25日,对于像我们一样因开战而滞留德国的900名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经过数月的谈判,纳粹政府同意用这些平民交换一群因敌对活动而困于北美和南美的德国人。我们万分欣喜地收到一封命令我们到瑞士边境的拉文斯堡(Ravensburg)报到的电报,那里距德累斯顿500英里。在那里,我们满怀期待地等待着我们的名字被叫到,急切地看着构成德国和瑞士边界的博登湖(Bodensee)。但官员检查名单时,我们的名字不在上面,一个纳粹官员直率地告诉家父,盖世太保,即纳粹秘密警察,显然已经决定不让我们获批离开。家父向边境的官员出示了命令我们参加交换的电报,但他们仍然拒绝签署必要的文件。
上帝将恩惠赐予那些忘记他的人,这样的恩惠是有尽头的,而我们在这里,与自由只有一百码的距离,只要在一份文件上签个字,我们就可以返回美国,免除后来所要承受的一切苦难。然而,这个签名被扣押了,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目睹这些美国人离去。
也许这仅仅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失误,因为后来在德累斯顿,我们得到保证,将获批参加下一次交换。也许是命中注定,随着艾森豪威尔的军队越过莱茵河,平民交换就此停止,但是,当我回首往事,却在其中看到了另一种安排。我的家人和我早已失去了与上帝的联系,我们只有努力取回上帝的赐福,才能再次享受到这份福气带来的自由和富足。
德军开始对不设防的城市发起无情的轰炸,先于1940年5月14日空袭鹿特丹,随后又轰炸了伦敦和考文垂,从而埋下了祸根。如今她正在收获苦果。英国和美国的大规模空袭正在袭击德意志帝国的一个又一个城市。德累斯顿目前幸免于难,这里挤满了来自其它不太幸运的城市的难民。
1945年2月13日傍晚,我正准备和一个朋友去他父母在市中心的家中吃饭,这时父亲从工厂打来一通电话:瑞士边境已经关闭,一些宝贵的相机本应在当天运往瑞士,但现在滞留在工厂里。他说,德累斯顿的工业区有可能遭到轰炸,为安全起见,他要把这些相机送到我们家里,安放在房屋的地下室深处,他要求我在现场接受委托。因此,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取消了共赴晚餐的约定,当工厂的人到来时,我就在家中,帮助他们小心地把一箱箱相机从沿着房子的陡坡上开出的72级台阶上搬下来,并把它们堆放在地下室里。
这些人走后,我的母亲和此时已经回到家里的父亲,以及我坐下来吃晚餐,但还没等到我们吃上一口,当地的民防站就传来了简短的通知,称英国飞机离该市不到20英里了。我们走到屋外,可以听见飞机的轰鸣声正在逼近。突然,在市中心,防空警报的阴森哀号在漆黑的城市上空响起。会不会轮到我们挨炸了?一种无助的感觉冲击了我,一介草民在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它出自空中投弹手的那双看不见的手。如果这次空袭真是冲着我们来的,那么下方城市中数以千计的人,在这一瞬间,必定是在呼吸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口气,或许,甚至我们自己也正是如此......
图2 别墅“圣雷莫”(San Remo),诺布尔一家在德累斯顿的住所 |

图2 别墅“圣雷莫”(San Remo),诺布尔一家在德累斯顿的住所
我们在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里准备了一个紧急防空洞,这个房间有一个通往花园的独立入口,并且在天花板上架设了特殊的支撑物,这样一来,即使房屋倒塌,我们也不会被掩埋,但我们在去往那里之前犹豫了片刻。我们能够听到城北和城南的飞机轰鸣声。迄今为止,当它们向南飞行时,都是在前往捷克边境附近的石油补给站的路上,也许我们会再次幸免于难。但突然间,两架轰炸机的机翼调转了方向并向城市汇集,镁光照明弹从天而降——可怕的“圣诞树”照亮了黑暗而恐慌的城市。
眼下毫无疑问:关乎我们性命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不顾一切地从台阶上奔向防空洞,高爆轰炸的第一道闪光使我们目盲,炸弹的第一阵爆破声在我们耳边回响。但是,炸弹落到市中心的时候,我们松了一口气。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头上的砖墙有多厚,天花板的支撑物有多坚固,我们自己周围有多少物理性防护。
空袭异常猛烈,一波接一波。炸弹现在倾泻在城市的其他地区,每时每刻都在逼近我们。听到一颗颗炸弹越来越近,每一次震荡都会让人更加难受,并使人惊恐地意识到,飞机正沿着不断扩大的圆圈盘旋在自己头顶上。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万事皆有可能发生。我周围的物理防护是毫无用处的。经由人手所造之物,现在正被他人之手所毁!
一枚炸弹在离我们一百码远的地方爆炸了,声音之大好似电闪雷鸣。楼上的窗户被震碎了。其它近处的爆炸所产生的震荡使房屋摇摇欲坠,地下室房间的门因气压差而不断被冲开。我母亲早已神经紧绷,这更加折磨了她的神经,于是我用后背抵住门站着,在爆炸引起的一阵又一阵气浪下支撑住自己。站在那里时,我却想到了《圣经》中关于耶利哥的故事(《约书亚记》6:20,《希伯来书》11:30),以及伟大的黑人灵歌中的歌词:“城墙轰然倒塌。”奇怪的是,此时我已有多年没听人讲这个故事了。我们的墙壁确实在倒塌,但倒塌的不仅是城市中的物质性墙壁,也有我们心中的墙壁——醉心于物质而造成我们与上帝之间产生的隔阂。
我才21岁,是一个沉迷于世俗生活的愚蠢青年。如果我当即死去,能在审判日对上帝说些什么呢?当我站在那里,意识到当下每一刻都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刻时,我知道我不配得到救恩。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主地产生宗教冲动。诚然,我曾不时地默默跟从他人去朝拜上帝,而且正如我先前提到过的,我也曾在家庭聚餐时做过谢恩祈祷,但我此前从未直接发自内心地祈祷。正是一次空袭唤醒了我,使我意识到有一位上帝存在,无论我生前做过何事,死后发生何事,我都要依靠祂。
20分钟后,突然间,严酷的考验结束了。不再有炸弹落下,飞机飞走了。数以千计的燃烧弹点燃了烈火,屋外的夜景亮如白昼。吹来了一阵强风,这是下方城市中巨大火势的热浪引起的,它反过来又助长了火势。然后,虽然夜色晴朗,但温热的大雨开始从天降下,这源于瓦砾中的那些柴堆,它们燃烧后使气温飙升,其中的水分冷凝而产生了雨水。我们在房子里奔波于各个房间之间,扑灭火星,几乎无暇去想象这座城市里发生的浩劫。
供电中断了,我们点起了蜡烛,这样便可以清扫碎玻璃,取下被撕碎的窗帘和帐幔。我们几乎没有碰过的饭菜里满是玻璃碎片,我母亲去厨房查看还剩下什么食物。然后,就在我们收拾桌子准备再次用餐时,我们听到了新一波轰炸机迫近的轰鸣声。没有防空警报响起,因为它们在第一次空袭中被尽数摧毁。我和父亲一时不知所措,难以置信地站在那里聆听。但轰鸣声有其规律,我们是不会搞错的。盟军空军对德累斯顿的空袭并未结束。我们呼喊着家母,再次奔向掩体。我当时在靠近楼梯口的走廊里,怀着刺骨的恐惧,听见炸弹那稳重的嘶鸣声直接朝我们袭来。我跌坐在地上,与此同时,一道强光照亮了房子,紧接着传来震耳欲聋的撞击声,令我的耳朵嗡嗡作响,知觉涣散。残余的窗户从窗框里蹦了出来,砸在对面的墙上碎裂开来,尖锐的残片溅射到我身上。这时,又传来了一波震荡,墙面灰泥的粉尘飘落下来,导致我鼻孔堵塞。一枚巨大的薄壳炸弹击中了距房子仅有80码的陡坡。这颗炸弹把陡坡炸了个底朝天,包括树木在内的一切都被炸毁了,爆炸的威力波及了房屋,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屋顶被炸毁了。如果炸弹再靠近几码,它的全部威力就会落在我们身上,这必将是我们的死期。
不知怎的,我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跑下楼梯,进入防空洞。这次我真的开始认真祈祷了。英国人在这第二次空袭中使用了他们最大的炸弹,就我们现在所知,除了后来对日本使用的两颗原子弹,这是有史以来人类在战争中使用的强度最大的一种炸弹。在先前投下的火光的指引下,皇家空军正在有条不紊地炸毁德累斯顿,将其一举击溃,作为对歇斯底里、死硬的纳粹分子的最后警告,使之停止徒劳的抵抗。
我从未向父母谈起过宗教,现在我也无法向他们解释我的感受。但在那绝望的几分钟里,世界似乎正在火焰中焚毁,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死去时,我跪了下来。我回想了自己的生活,就像一个时常感到死期将近的人那样。我想到了我们在美国的家中度过的美好时光,想到了我们是如何跨过种种危险而得以生存至今的,想到了我们的处境逐渐恶化,想到了三周前我们无比接近自由的那一天,想到万事的走向似乎正在逼近某种顶点。
我害怕呼求上主的保护。这些年来,在万事顺遂之时,我一直在躲避他,而现在,当我处于极端的处境下,却发现对祂而言我是个陌生人。为了拯救自己那不配得救的生命,我试着找出一些言词来祈求祂,但我只能谦卑地呼唤:“求你救救我们,亲爱的主!求你救救我们!”
在三十分钟的时间里,房屋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爆炸而摇晃。我们正上方的“圣诞树”之火在烟云中闪闪发光,为即将到来的一波波轰炸机勾勒出城市的边界。
当飞机的轰鸣声终于渐渐远去,更加令人耳聋的寂静顿时取代了爆炸声,我们蹑手蹑脚地走上楼去。我们又一次必须去做一些紧要工作。火焰引发的强风吹向城市,房屋在狂风的吹拂下摇摇欲坠。空气中弥漫着活跃的火花,我们为拯救我们的房子奋战了一个小时,以极微小的优势赢得了这场战斗。整个夜晚,我们都在等待投弹手回来。整个夜晚,我们目睹德累斯顿熊熊燃烧,我们的下方陷入一片火海。当我们望向这座城市时,能感觉到火焰在烧灼我们的面孔。对于可怜的民众,我们无能为力。直到可燃物耗尽,这场大火会一直燃烧下去。
大约早上七点,我离开家,试图找到一间商店买些面包作早餐。在林荫大道上,触目惊心的景象映入我的眼帘。尽管道路很宽阔,但它的两侧之间挤满了徒步进城的行人。他们的面孔被烟尘熏得发黑。他们的眼睛下面有白色的条纹,那里的污垢已经被泪水和汗水冲刷殆尽。男人和妇孺在这浩浩荡荡的人群中挣扎着前行,他们推着手推车、自行车、婴儿车、儿童玩具车,以及任何足以装载少量被褥或珍贵家当的载具。有些人根本没有带上任何东西,他们在杀戮中只保住了身上穿的沾满煤烟的破衣烂衫。在这里,有一些伤员裹着毯子走来走去,他们的衣服已经被爆炸的力量烧毁或撕碎了。一些人在吐血;另一些人一边行走一边痛苦地抽泣,并紧紧地依偎在同伴身上寻求支持。孩童在恸哭,大人却沉默不语,许多人仍然处于震惊状态,他们惊呆了,无法认知到自己的损失有多么严重。他们不仅将家园的废墟抛在身后,
还抛下了亲人的尸体。道路的前方是难民的不安定生活。
怜悯之情涌上心头,尽管我知道这个社会跟随希特勒和他的军头们走上了罪孽深重的道路,一条伤天害理的道路,在德累斯顿的那个早晨,我目睹的是上帝对这个社会的审判,。
在营业的食品商店中,店主们正在分发他们的存货。大多数幸存者身无分文,也失去了他们的配给卡。我观望了几分钟,然后没有买面包就回家了。我甚至没有求取任何食物,我们家的地窖里还存有一些。
随着那一日逐渐成为过去,我们的几位朋友想方设法从城里来投奔我们家。我们乐意向他们敞开房门,并尽力安慰蒙受损失的他们。由于我哥哥早已去了乡下务农,当时我们家只有三人住在这座大房子里,而在第二天结束前,我们已经为20多人提供了住所。
次日,我和父亲骑上自行车,穿过仍在冒烟的废墟,来到我们的工厂附近。这个工业区几乎完好无损!但就在我们到达那里时,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我们立刻躲了起来,因为约有一百四十架美国轰炸机前来执行任务。然而,他们集中攻击了易北河上的剩余桥段及其周边地区——不知为何,那些地方先前被数百架英国夜间轰炸机忽略了。我们的工厂区,显然不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又一次免受殃及。
在遭受轰炸的城区,竟然有人能逃过一劫,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在去往工厂的途中,我们看见一个我认识的姑娘的家成了废墟。当我们驻足于那里,她和她的母亲从邻居家走了过来。她们已经遭遇了两次轰炸,但每次都死里逃生。现在,当我们返程时,发现第三次空袭再次袭击了同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它残余的最后一块墙壁在火海中坍塌了。然而,她们又一次设法逃进了掩体,而且毫发未损。这种奇迹般的逃生是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
我为自己的幸存感到受宠若惊。我知道我的头顶上有一只无形的援手。我觉得一定是上帝放了我一条生路,因为我对他有用处。我目睹了我家的陡岸边上由两颗薄壳炸弹轰出的巨大坑洞。我自问,那个投弹手在10000英尺的高空以每小时200多英里的速度飞行,如果他按下投弹按钮迟了十分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事。
第二周,当我下山到城里去寻找我们厂里的几位工人时,我查了一下那个朋友的房子,要不是父亲的电话打破了我的计划,原本我会与他共进晚餐。那座房子已被炸成一片残砖断瓦。我没有发现他家人的踪迹。过了一会儿,我遇见了他们的一个邻居,他迷乱地摇着头告诉我,我的朋友、他年轻的妻子和他的父母都死了。第一波轰炸中的一枚炸弹命中了他们的房子,他们毫无躲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