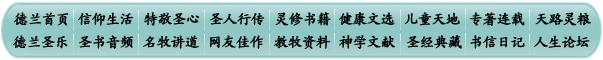我第一次看见亚当与厄娃在乐园中行走。动物跑来迎接并跟随他们,但它们对厄娃显得比对亚当更熟悉。事实上,厄娃更关注大地与受造之物。她比亚当更频繁地低头张望、环顾四周。她似乎是两人中更好奇的那一个。亚当则更沉默,更沉浸于天主。
动物中有一只比其他更紧跟着厄娃。那是一个异常温顺可人、却又狡黠的生物。我不知道有任何其他生物可与之相比。它身形细长,毛色光亮,看起来仿佛没有骨头。它用短短的后脚直立行走,尖尖的尾巴拖在地上。头部近旁长着短短的小爪,头圆圆的,面容极其机灵,狡黠的舌头总在不停活动。脖颈、胸膛和腹部呈淡黄色,背部则是斑驳的褐色,很像鳗鱼。它大约有十岁孩子那么高。它总是围着厄娃转,如此会哄人、聪明、敏捷又灵活,以致厄娃非常喜爱它。但在我看来,它身上有某种可怕的东西。即使现在,我仍能清晰地看见它。我从未见过它触碰亚当或厄娃。在堕落之前,人与低等动物之间距离很大,我从未见过最初的人类触碰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它们对人确实更信任,但总是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当亚当与厄娃返回那片光耀之地时,一个发光的人影站在他们面前,状如威严之人,须发闪亮银白。他指向四周,寥寥数语,似乎将万物交给他们,并吩咐他们某事。他们并无惧色,而是自然地聆听着。当他消失后,他们显得更满足、更快乐。他们似乎更明白事理,在万物中看到更多秩序,因为如今他们心怀感恩,但亚当比厄娃更甚。她更专注于他们当下的幸福及周围的事物,而非为此感恩。她不如亚当那样完全安息于天主,她的灵魂更专注于受造之物。
当亚当与厄娃返回那片光耀之地时,一个发光的人影站在他们面前,形貌如威严之人,须发闪亮银白。他指向四周,寥寥数语,仿佛将万物托付于他们,并给予他们某些吩咐。亚当与厄娃并无丝毫畏惧,只是聆听着。当那身影消失后,他们显得更为满足,神情中洋溢着更深的喜乐。
他们仿佛对万物的理解得更透彻,觉察其中秩序井然,因他们此刻懂得了感恩——只是亚当的感恩之心,比厄娃更甚。厄娃的心神仍更多地缠绕于现世的福乐与周遭的万物,却疏于为此感恩。她未能如亚当那样全然安息于天主,她的灵魂更系恋于受造之物。
我看见亚当与厄娃在乐园中行走了三圈。我又看见亚当站在那座发光的小山上——那里是天主趁他沉睡时,从他肋间取出一根肋骨造成女人的地方。他独自立在树下,整个身心沉浸在感恩与惊奇之中。
我看见厄娃在知善恶树附近,仿佛正要经过,那只熟悉的动物伴在她身旁,显得比以往更狡黠、更爱嬉闹。厄娃被那蛇迷住了;她对它格外倾心。它爬上知善恶树,直到头与她的视线齐平。接着它用后脚攀住树干,将头凑近她的头,对她说:如果她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便不再受束缚,将获得自由,并明白人类的繁衍将如何实现。亚当与厄娃已领受“生育繁殖”的命令,但我明白他们尚不知天主愿意如何成就此事。我也察觉——倘若他们那时已经知晓,却仍选择犯罪,那么救赎便不可能实现。
厄娃此刻变得更多思虑。她似乎深受那蛇所许诺之物的欲望搅动。某种低下的堕落之物攫住了她,令我感到不安。她转头望向仍在树下安静站立的亚当。她呼唤他,他便向她走来。
厄娃起步去迎他,却又转身返回。她的动作显得不安、犹豫。她再次起步,仿佛打算经过那树,但又一次犹豫,转而从树的左侧靠近,躲到树后,被长长垂落的树叶遮掩了身形。那树上头宽阔、下头窄小,枝叶茂盛的枝条一直垂到地面。就在厄娃伸手可及之处,挂着一串异常精美的果子。
此时亚当已走近。厄娃伸手抓住他的手臂,并指向那说话的动物,亚当便听它说话。当厄娃将手搁在亚当臂上时,那是她第一次触碰他。他并未回碰她,但他们周身的光辉却渐渐黯淡下来。
我看见那动物伸爪指向果子,但它不敢贸然为厄娃摘取。然而当那渴望从她心底升起时,它便摘下那簇五枚果实中居中最美的一枚,递入她手中。
此时我看见厄娃靠近亚当,将果子递给他。倘若他拒绝,罪便不会发生。我看见果子在亚当手中仿佛裂开。他在其中看见图像,仿佛他同厄娃被教导了本不该知道的事。果肉呈血红色,布满脉络。
我看见亚当与厄娃失去光辉,身形缩小。犹如太阳西沉。那动物滑下树,我看见它四肢着地跑开了。
我并未看见他们如我们今日进食般将果子送入口中,但果实在亚当与厄娃之间隐去了形迹。
我也看见,当蛇仍在树上时,厄娃已犯了罪,因她的心已顺从了那诱惑。那一瞬间,另有某种领悟临到我,我却无法清晰复述:那蛇仿佛是亚当与厄娃意志的化身,成为他们可凭之成就一切、拥有一切的某种载体——而撒殚正由此路径侵入了世间。
罪并非仅因吃下禁果便告完成。然而那棵树——它的枝条深深扎入土中,发出新芽,在堕落之后仍持续如此——传递了一种更绝对的繁衍观念,一种以与天主分离为代价、植根于自我的感官培植。于是,与悖逆一同,从他们的放纵中生出了受造物与天主的隔绝、那种在自我内并经由自我的栽种,以及人性中那些自私的私欲偏情。人若只为那果子所带来的享受而使用它,就必须接受其行为的后果——本性的颠覆、败坏,连同罪恶与死亡。
亚当在厄娃受造后所领受的、那源于天主且借由天主运作的纯洁与圣洁繁衍的祝福,因这番放纵而被收回——因为我看见,就在亚当离开山丘走向厄娃的那一瞬,上主伸手按住他的脊背,从他体内取走了某样东西。自那被取走之物中,我感到整个世界的救恩终将由此而来。
有一次,正值圣母无原罪始胎庆节,天主赐我关于那奥秘的神视。我看见全人类的肉身与灵性生命都被封存于亚当与厄娃之内。我看见这生命因堕落而腐坏,与邪恶相混杂,恶天使也因此取得掌控它的权柄。我看见天主圣子自高天降下,用一柄形如弯刃之物,在亚当尚未犯罪时便取走了那祝福。同一时刻,我看见童贞女由亚当肋旁而出,如一小片光云,通体辉煌,升向天主台前。
因着吃下那果子,亚当与厄娃如饮烈酒般迷醉了,他们对罪的同意在他们生命中造成剧烈的改变。那蛇的毒性已侵入了他们生命内——蛇的本性渗透了他们的本性,如同莠子混入了麦子。
作为惩罚与修复,割损礼从此被设立。正如葡萄枝需经修剪,才能避免狂野生蔓、酸涩,不结果实,人也当经历此礼,方能重获那已失去的成全。
一次,堕落的补赎借象征性图像显给我看:我看见厄娃正从亚当肋旁生出时,竟在那一刻已伸长脖颈去够那禁果。她随即飞快跑向那棵树,伸臂将它紧紧抱住。而在另一幅对应的图像中,我看见耶稣由无玷童贞女诞生。祂径直奔向十字架,伸开双臂拥抱了它。我看见人类的后代因厄娃而陷入昏暗与毁坏,却借着耶稣的苦难重得净化。
藉着补赎的苦痛,那对自我的邪恶贪恋必须从肉身中连根拔除。圣保禄书信中那句“婢女的儿子不能同为承继者”,我常领会这是指肉欲以及对它的奴性屈服——正以婢女的形象作为象征。
婚姻乃是一种补赎的境遇。它呼召人祈祷、守斋、施舍、舍弃自我,并怀有扩展天主之国的意愿。
亚当与厄娃在犯罪前的生命,与我们如今这些可怜悲惨的受造物全然不同。自他们接受禁果那刻起,他们吸入了一种物质性的生存状态。灵化为质料;肉体则沦为工具、盛载的器皿。起初他们与天主合一,他们在天主内寻见自我;但后来他们任凭自己的意志掌权,从此与天主分离。而这自我意志,正是转向自身的追求,一种对罪恶与不洁的贪恋。
因吃禁果,人背离了自己的创造主。那情景就像他把整个受造界吸入了自己体内。一切创造的权能、运作与特性,连同它们彼此之间并与整个自然的交融,都在人里面化作了形态与功能各异的物质事物。人曾经享有统辖自然的王权,如今他内里的一切反倒成了自然本身。如今他成了自然的奴隶之一——一位被征服、受捆锁的主人。他如今必须与自然挣扎缠斗……只是我无法说得更清楚。
这就好像人曾在天主——他们的创造者与中心——内拥有一切;如今他却把自己当作中心,而万物反倒成了辖制他的主人。
我看见人的内在、他的各个器官,仿佛都嵌在血肉里,呈现在受造界那有形、可朽的形像之中,连同它们彼此的关联——从星辰直到最微小的活物,无一例外。这一切都作用于人。他与万有相连;他必须行动,与它们搏斗,也因它们而受苦。只是我无法说得更清楚,因为我自己也属于这堕落的族类。
人的受造,本是为了填补堕落天使留下的歌班空位。倘若亚当没有堕落,人类的繁衍只会持续到堕落天使的数目被补满为止,之后世界便会终结。如果亚当与厄娃曾见到哪怕一代无罪的后裔,他们也就不会堕落了。
我确信:这世界将持续存在,直到堕落天使的数目被填满,直到麦子从糠秕中被完全收割。
一次,我蒙赐予一个关于罪恶与整个救赎计划的宏大而连贯的神视。我清晰分明地看见一切奥秘,却无法将这一切诉诸言语。
我看见罪从天使的堕落和亚当的堕落延伸出来,如同枝蔓般伸展直至今日;我也看见那为修复与救赎所做的一切预备,一直延伸到耶稣的来临与死亡。
耶稣向我显示万物的奇特混杂、一切受造物的内在不洁,以及祂从太初就为它们的洁净与复原所做的一切。
在天使堕落之际,无数恶神降临大地与空中。我看见许多受造物受其忿怒的影响,以各种方式被它们占据、受其控制。
最初之人是天主的肖像,他如同穹苍:万物在他内浑融为一,万物与他共成一体。他的形态实为天主原始肖像的重现。他注定要拥有并享受大地及一切受造物,却须从天主手中领受,并为这一切献上感恩。
然而,人本是自由之身;因此他必当经历试炼,因此他被禁止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
起初,大地坦荡,辽阔无际。直到那山丘——亚当曾驻足其上的发光小山——拔地而起,那遍开白花、我曾见厄娃立于其间的山谷沉降为壑时,那败坏人者便已近在咫尺。
堕落之后,诸象皆改。一切受造的形态都在自我中萌发,又在自我中消融。那原本整全的,裂为繁杂;受造物不再单单仰望天主,每一物都转向自己,以自我为中心。
人类起初是二人,继而三人,最终多不可数。他们曾是天主的肖像;堕落之后,却成了自我的肖像——这肖像乃是从罪中出生的。
罪使他们与堕落天使相通。他们在自己内及周遭的受造物中寻求一切益处——堕落天使与这一切皆有联结;从这无尽的混杂中,从这高尚的官能沉沦于自我、沉沦于堕落的本性中,便滋生出诸般的邪恶与苦难。
我的净配将这一切清晰、分明、易懂地显示给我,比人观看日常事物更清晰。那时我以为连孩童也能明白,可如今我却无法复述。
祂向我显明了整个救赎计划及其实现的方式,以及祂自己一切所行的。
有人说:“天主无需降生成人,也无需死在十字架上;祂既是全能,自可以别的方式救赎人类。”此话实是误解了天主的完美, 我看见天主所做的,正符合祂那无限的完美、仁慈与公义;本无“可以不必”的道理——祂行其所愿行,是其所本是!
我见默基瑟德如同天使,是耶稣的预像,是世上的司祭;这司祭职源自天主、超越时间,他是那永恒神品中如天使般的司祭。我看见他为人类家族作预备、立根基、建体系、辨亲族,并如向导者般带领他们前行。
我也看见哈诺客与诺厄,二人各自标志着天主计划的特定阶段,并承行他们被托付的使命;另一面,我看见地狱的权势从未止息,以及那属尘世、顺肉欲、出自魔鬼的偶像崇拜——其形态变幻无尽,所蔓延的毒果也遍处滋生。
我看见罪与救赎那先知性的预像——它们各按其独特方式,共同揭示着天主的大能:罪以反照的方式显明天主公义的法则与对救恩的主权,而救赎则以直接的方式彰显天主慈悲的满溢与胜利的权能——这正如人本身,无论处于何种境况,仍是天主的肖像,承载着回归原初神圣模样的可能。
这一切都从亚巴郎直到梅瑟,又从梅瑟直到众先知,连同他们彼此相系的脉络、以及与我们这时代相应预像的关联,——显明给我。
例如,关于“为何现今司祭不再缓解病苦、施行医治,为何这能力不在他们权下,或为何今日成效与往昔迥异”,正是与旧约中这些异象紧密相连的。
我确实看见先知们拥有这份司祭职的恩赐,并且那施行恩赐时所取的形式及其象征意义,也启示给我。
就以厄里叟将自己的手杖交给革哈齐、放在叔能妇人已死孩子身上的事迹为例。那手杖在属神的意义上承载着厄里叟的使命与权能——它如同他的手臂,是他权柄的延伸。正是在这里,我领悟了主教牧杖与君王权杖的内在意义与能力:倘若在信德中运用,它们便能以某种方式将主教与君王与赐予他们尊位的天主联合,同时也将他们与众人分别开来。
但革哈齐的信德不坚,那母亲认为唯有通过厄里叟本人才能获得救助;于是在厄里叟来自天主的权能与其手杖之间,介入了人的妄断,手杖便未治愈。
而后我看见厄里叟俯身祈祷,将双手、口唇与胸膛都贴在那孩子身上,如此,男孩的灵魂便回到了他的体内。
我蒙受启示:这治愈的方式正是指向并预表耶稣的死亡。在厄里叟身上,凭着信德与天主赐予的权柄,人身上一切自堕落以来被关闭的恩宠与赎罪之途——即头颅、胸膛、双手与双足所象征的——得以重新开启。
厄里叟将自己的身体,如同一个活生生的、象征性的十字架,伸展在那男孩已失去生命、已封闭的形体之上。藉着他那充满信德的祈祷,生命便得以恢复。他以此赎补并补偿了那对父母曾因自己的头脑、内心、行为与脚步所犯、导致其子死亡的罪过。
就在此刻,我眼前浮现出耶稣的圣伤及祂在十字架上死亡的景象,由此我得以窥见耶稣与祂的众先知之的和谐。自耶稣被钉十字架以来,那医治与补赎的恩赐便充充满满地临在于祂所建立的教会的司祭之中,也普遍地运行于信实的基督徒之间。这恩赐的深浅,正取决于我们与基督契合的程度——我们愈是活在他内、愈是与祂同钉十架,那恩宠的通道、即祂神圣的五伤,就愈是向我们开启。
关于覆手之礼、祝福的功效,甚至手在远处所能施予的影响——这一切奥秘,我都藉着厄里叟那象征“手”的权杖得了领悟。
至于为何今日司祭如此少行医治与祝福,一个深具意义的图像启示给我:那关键全在于是否“肖似耶稣”——一切恩宠的涌现与功效,无不植根于此——即对基督的肖似。
我看见三位匠人制作蜡像。第一位使用美丽的白蜡,他技艺娴熟又聪慧。但他自负,基督的形象不在他内,他的工作毫无价值。第二位用的蜡不如第一位的白,他的怠惰与任性毁了一切。他什么也没做成。第三位笨拙不巧,但他以纯朴之心、极大勤勉地继续用普通黄蜡工作。他的作品卓越,栩栩如生,尽管面容粗糙。
我看见那些誉满四方的宣讲者,虽凭俗世的智慧夸口,所行的却归于徒然;倒有许多贫穷、未受学问的司祭,仅凭着其司祭的权柄,便施行了治愈与祝福的恩典。
当这一切显示给我时,我宛若身在学堂。我的净配使我看见祂从受孕至死亡如何受苦,时刻在赎偿罪债、时刻在为罪恶作补赎。这景象,我在关于祂一生经历的异象中亲眼目睹。
我也看见,因着为他人献上的祈祷与所受的苦难,许多在世上未曾行善的灵魂,竟能在临终时刻悔改并得蒙救赎。
我看见众宗徒奉派前往世上大部分地域,为粉碎撒殚的权势并广施祝福。而他们被遣往的那些地方,恰恰曾是受恶者侵害最深之处。
耶稣藉祂圆满的赎罪,为一切已领受或将领受祂圣神之人,赢得了制胜撒殚的权能,并将此权能永远稳固地赐予他们。
我蒙启示而领悟:“你们是地上的盐”这句话,正指向那种藉祝福将大地多方区域从撒殚权下夺回的权柄。盐因此成为圣水的要素之一。
在这神视中,我还看见:那些属血肉、属世间的琐碎规条与虚文缛节,竟被人以近乎病态的严谨、甚至狂热的精确,一丝不苟地遵守着。我看见了因祝福被颠倒而反扑的诅咒,也看见了撒殚国度里所伪造的奇迹;我还看见了对受造自然的崇拜、各种迷信、巫术、催眠术、世俗的艺术与科学,以及一切用来粉饰死亡、使罪显得诱人、令良心昏睡的手段——而这一切,恰恰被那些蔑视教会圣礼、视之为可任意替换的迷信形式之人,以严苛至极的准确度、甚至带着宗教般的狂热在实行。
然而,吊诡的是,正是这班人,却将自己整个的生命与一切行动,全然屈服于另一套人为的、仪式化的规条之下。惟独对于那“天主而成为人”的基督之国,他们漠不关心。世界得了无微不至的侍奉,而对真天主的敬拜与事奉,却被他们可耻地搁置一旁、冷落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