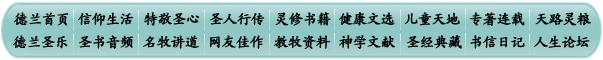|
六十九 致赵主教 雷神父起程赴他传教的新地区绍兴之前,赵主教那里收到了一份「传教区思想备忘录……」 该备忘录在措词上.不赞成雷神父的基本态度……在年退省中,雷神父给赵主教写下了这封壮丽的信。此信没有得到回音。另一副本由汤作霖神父寄往罗马,充实传信部所有的诉讼记录。 此信写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在雷神父年退省宁,地点是宁波。 主教: 我恭闻「面对某些意见,确定教区思想及态度的备忘录」后,已有两个月,我自己觉得忧心忡忡。最初,我曾愿答复您,向您谦逊地陈明我的思想;而后,我又想回答您,向您掩饰我的思想,向您说教区的这种想法曾经是我的想法,而现在还可能是我的想法。我好歹地在表面上接受文字的辞句,而不接受其中的精神,所以我的想法仍然……一方面由于害怕失去您信赖的心情,阻止我向您说出我所想的实情;一方面由于畏惧失去天主宠爱的情绪,阻止我向您说出我所谓不真实的思想。在这害怕及畏惧之间,我战战栗不安,终于在我再三反省之后的结果是:您既然未曾要求我回答……我就什么也不回答。 但是我的良心却不让我平安,在您慈爱之前,主教大人不断地向我证明这份慈爱,从您给我打开了教区之门的日子起,我便感到有义务向您将我的全部思想表达出来:因为无论怎样,我也没有办法向所有人隐藏我的思想,隐藏是不会长久的,因为我个人不知不觉中,将我的思想从我的语言或行为流露出来。我的思想对您不肯清楚坦白的陈明,既不怕向人泄漏,岂可向好天主代表隐瞒。 特别是昨天,在默想天主以及对祂的义务时,我终于决定,放弃我的全部疑虑,将这些思想写给您。我特别决定要说出的,乃是反省使我所要缄口的,我以为这是巴赛所说的「害怕招致不洁的恐怖,及卑鄙的颤抖」。 我是耶稣基督的司铎,为了害怕看见一张不愉快的面孔,为了害怕或许失去我上司的看重,而竟能这么长久阻止我完成认为是义务的事,真羞煞我也! 给予我写出我思想的信心,乃是我所决定的时间与环境,在避静的时候,良心的声音,比起普通时间更清晰洪亮,比起普通谈话来,更为明白通畅——这时死亡的思想,审判的观念,对全部责任的感觉,都比平时更活泼,也具有更大的力量,更能指导我的行为。这时天主的圣爱在更近处驱使我——我在避静中给您写信的这个事实,也更给我希望,使您肯相信我所陈述的诚意,毫无保留。今天我所做,就如今晚我该出现在天主的法庭前一样,没有任何人情的顾虑,而且还坚强地将这些情面全部践踏在脚下。 一、爱国说 我上面的微妙思想,可以综合在两句话内:(一)中国的教友有权利更有义务成为爱国者,与欧美教友「一般无二」。㈡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像欧美的司铎一样行动和谈论。他们的义务和我们的义务,所有的范围与界限是这样好好规定了的。并且,在这界限内我们和他们所要做的,将是一种义务或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特许。 现在这些义务,在欧美各国,并不只在于纳关税和缴房捐。也不只在于忠守拿破仑的规定,及不违警而已。人们更不能将这些规定划入慈善事业或社会公益事业:这些一事业虽然在欧美好教友那里,在他们爱国的情操上,多次占有一部份势力,但首要是属于人道主义的。他们多次是在他们国家界线外,展开这些活动。在此这实际上已不是所谓爱国的本意了。这已经是为自己祖国祈祷的一种爱国行为。恐怕这些事,在中国的教会内,人们做的很少或根本没有做, 爱国,特别如同天主教数世纪所形成的爱国,如同现在存于这些愿意生存而又有自我意识的各民族中的爱国,它首先是一种爱情,是一种对忠诚及牺牲的创造兴奋,是一个伟大的理想,所以也是一个伟大的力量。这不只是一个公共利益的问题,而且要超过它。这是一种听列国歌时,内心热血沸腾的情感,见到国旗使最高傲的人脱帽致敬的强风。 这种力量是一种高贵气质。在欧洲人们说这力量温柔地生自天主教教义,就如一朵花。而这种高贵发展成为一种力量,也恐怕是一个国家的更坚牢的防线。 因为这是一种高贵,也是天主教的高贵,因为这也是社会力量的广大累积处所。各国圣职,我以为尤其是法国的高贵圣职所做的一切,就是在那不存在或己不存在的地方,提倡这爱国的力量;在那假寐的地方,唤醒这力量;在那衰败的地方得复兴这力量。 但爱国,对国家来说,不仅是一种力量,爱国为教会是一种力量。反过来说,抵制这种力量也会产生相等的效果。它是一个杠杆,能撬起群众;它是一个磁石,能吸引人灵。因为它是高贵的情操——强大的武器,能使抵抗的人和有成见的人屈服。就是这力量超过其它的一切事物(我以人为的观点来说)它给法国的教会领回一部份已失散的教徒。人们对法国的圣职人员深深感激,不只是感激他们在三年战争期间无可此拟的爱国心,而且感激他们在和平时期内更艰苦的爱国心。因为当时唯独以圣职人员为首的天主教徒,倚仗他们的言论,抵抗国际主义的汹涌波涛,甚至曾被诬告为战争种子的撒播者,并以祖国的激烈思想,被诽谤为保持一八七0年的古老怨恨者。 的确,这一切是这样清楚、正确、无人怀疑,因此我不愿引伸、言明、提出在我记忆中现有的千百个例子。 这为欧洲教友是德行的,为中国教友也该是德行。这个为什么对欧洲圣职界是一个光荣的,对我们圣职界就成了一个缺点呢? 对于我们中国人的爱国,可能怕发生偏差的一切疑难,我可以简单答复:这更是对他们有教育义务的一个理由。我们并不能因不知道便予以取清,也不能因试将它减到最低限度而阻止他们超越界限。正相反,爱国要扩张,要完全独立演变,这种情绪越是在我们以外长大发展,将来偏差越可怕,教友们自己不知不觉,但事实上已离开教会。在这里虽然还没有成为决定性的,但难道该给它时间,让这良心上的可怕情况形成吗? 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够多了,为了这神圣的诉讼,我们付出生命,它该胜诉或败诉,由这些可疑的回避很容易引出隐匿的敌意。法国天主教徒及圣职人员的古老态度,现在还使法国忧苦,虽然这些圣职人员对于政治,政府的变动不太计较;不只一个国家同法国受到猜疑和反对,在这反对下接受了劳工运动和工会运动。实在,人们又悔改那反对的态度,而听从教宗的劝告,但还不是所有的人。而现在应该艰苦地一块一块地收复敌人听侵占的地区。 关于我们应有的动向,我言明我的思想,为此,我甘冒备忘录所谈到的危险,备忘录上说:「应该不使教友们参加一种不自然的,喧哗的爱国主义,这意味着偏袒与激烈的爱国主义,并将爱国与恨外国人、抵制外货,混为一谈……等等。在公开场合会议的爱国行动,容易使人疯狂」。 首先,这些喧哗的示威多少总有些不自然,这更好说是由于一种爱国心所驱使,而不是他们适当的表达,但这也不只是在中国特有的现像;还有,这激烈的爱国主义并不像它的名称所指的那么严重。人认为不管有理或没理,为本国该在这事件上自怨自艾,便不会再仇恨外国人了;最后,也不可斥责他们抵制外国货,因为这种观念是中国人在欧洲学来的……单凭以上情形是不容易观察实情的,这些夸张(不必这样,也不是在听有的情况中)似乎仅仅「在我们这里」发生为我们值得可笑。当我们不以为怪时,我们就把它当做软弱的通病吧,它总不会对我们造成反感和恐怖;从这争点上,我们不要梦想削弱欧洲天主教徒对于谨慑守法或忠实纳税上所有的爱国心。有人要说由于这些错误,在中国可能有悲惨的结局,并举出一些实例,首先可以答复这问题说,如果仇恨外国人能在此产生一些骚乱和屠杀,似乎这危险性很小,甚至不会存在。这里的人究竟受过教育,是文明人(老西开的历史就是很感人的文明例证)正是如此,人们对抵制外国货和罢工,都采取文明的方法。此外所带来的破坏比在欧洲少的多。但是不要把事情向最坏的地方的地方解释,布尔日人的)早祷,西西里人的晚祷末曾使法得及西西里的教友们放弃由他们错误所激发的爱国心,也没有使他们的司铎处罚这爱国心。 谈到激烈的爱国主义……啊,主教,但我见到了一些传教士在唱爱国的歌曲时,全身颤抖如癫痫病人一样,在唱完之后,他们本国的主教和司铎也感动的鼓掌。但激烈的爱国主义,在议事的聚会争辩时,是可默许的,也几乎为所有的人所惊呀,除非为中国人例外。另外一次,我在「法国——光明」杂志上,阅读了一篇耶稣会布罗神父在里昂圣鲁意教堂发表的演词。我并不说它不好;我可以说这演讲在自己国内能有好影响。我只是证明它属于最高度的激烈爱国主义,并且这演讲词在开罗有两个「许可出版」的名义,经由里昂天主教的印刷厂印出。请您准许我把在开罗以外所发表的几篇讲演的印象同上面的演说比较一下。在开罗以外的演讲「只是向外教人」说,中国的得救在天主教教义内……不幸的是这小册子的题目是:「救国」并在封面上画上两个中国国旗。所以这小册子虽有「出版准许」,但遭受猜疑,多次很不受欢迎——不只一位可敬的主教摇着头说:「为什么他常搞政治呢?」上面所述就是个活生生的事实:一个本国教会的思想和一个外国传教区的思想相反……此外又如比国人平常怀疑法国人是盲目的热情爱国者。法国人在这事上,对意大利人也说同样的话(而且还是在司铎之间)。除非有一天,人们开始想到自己也有错,只有那时人们才不致在国籍问题上构成大错。就加法、比、义三个国家,今天已结为同盟,大概不会互相开火攻击,尚且如此! 我可以这样无限制地继续写下去。总而言之,这感触很生动,这观察很困难。我以为,我们具有两个观点及两种尺度;似乎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行为,在夸越国界之后,就不再使它产生同样的印象,发表同样的判断。但是,在一切正义中,中国比我们出生之地,更有权力得到宽待,因为中国是个外教的国家——并且它对将来有信心,因为它要有一个基督化的未来,所以,若我们肯协助,在天主护佑下,它会此现在更好。 在这一切反省之下,仍然还存有这问题,假如爱国心步入歧途,在中国,由于不同的天性——本质上——仍然很危险,尽可能不受到指责,这将来仍然是错误,而不是爱国的事(如在欧洲,我了解实倩)不是脱离现势的司铎,他可以管理这个,一定不行。如果暂时压制这爱国心,这只是表面的,就如人将蒸气放在热鐄里,用铁箍的力量封住。但有一天热镘要爆炸,并且「将来它的灾情惨重」——另一种办法,就是谁若愿利用这种本身良好,而又合法的情感,在看到这事发生的国里,把它看做是一种美德(参阅迈谢枢机),赖天主助佑,他将来在手中只有运转机和汽机的活塞.如果他不能阻止一切祸患,一切过失,他依仗天主的协助,并按照应有的条件别将来能成为这力量的调整器,在轨道上保留这股力量,而引导这力量向往教会…… 由这两个情况,我已能指名道姓地举出具体的例证,但是,明显地,我们只是处于这把握中国伟大运动的曙光之中。就如这运动相继地把握了所有的其它民族。并使这运动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国家,促使在国家中生出一般爱国的力量,来扩展国家的生命。真的该放弃这力量吗?让这股力量继续滋张,来反对我们吗? 唉,如果我们不疏忽这力量,甚至也不相反这力量,我们像法国、比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的主教一样,将这力量作成我们的一种武器,来「为天主作战」中国教会的未来该如何呢?如果我们放弃了旧作风,我们已经不能再为我们隐藏这些一裂隙,那时,天光的晨曦该是多么美好呢,我们坦诚地下到平原,我们置身在民众之前,引导他们,使这个有前途的民族,走上伟大慷慨的境界——这并不指要参加什么政治会议及演讲等等。我重复的说,我们权利和义务的界限,在原则上,是同欧美司铎一样的。只是这个,一切就是这个。 天主优待了我,「我虽然是一切人中最小的,不堪称为门徒,使我与这个民族来往,比别人更多,我参加过很多外教各个会社,藉此与他们的心灵有过更亲密的接触。 这十七年传教生活给我所留下的印象,极清楚的印象,对于天主之国来临于这些人民最根本的阻碍——我不说是唯一阻碍——乃是「国家问题」;按人的说法来讲,除非有一奇啧出现,使教外百姓与教会分开的障碍是无法打破的,只有由我们继续努力才可以把它撤除。 因此,若真正的爱国心在欧洲教会是可赞美而也赞美过的,对中国的教会也有必要,这是人为的必要条件之一,使天主教在百姓中生根,引导群众进入教会的怀抱。 关于这一点,人们也要回答我说,中国圣职虽容许本地人有辅佐地位,但是并不能算作中国人的圣职。在和平时,要求一种比同情还更多的事;在战争时,要求一种明智的中立,这乃是要求人情上不可能的事。尤其备忘录对这问题说的不正确。假如一个比国圣职在法国创办法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人们会想象得到吗? 而且法国领事要说什么……公使要说什么呢?…… 由以上看来,这备忘录内的一切要点是有一连串逻辑连系着,我想把第三点放在第二点以前。 二、国籍圣职 备忘录首先对于成立完全国籍圣职,毕出了两个切实的理由:罗马的指示与事实的迫切……我以为由第一点中生出的结论可以加上成为第三个理由,只有本地圣职才能了解,深入并归化他本民族的灵魂。教会整个的历史也都给我们证明,在欧美没有见到一个国家,是在外国传教士管理之下而归化的。以上的话很动人。 如果主教大人怀疑一个完全国籍圣职,为达到一个地方的皈依(不是指分散各地的单位而是指一个地区)有其「绝对」必要性。我愿同钩座一起重提向万民传播福音的历史。其结论有如事实。所以对中国该有什么想法呢?中国不只是在国籍上与我们不同,而且在种族上也有区别,我们喜欢指出它对于外国人的多疑易感性。 由此而推论出的结论是传教士的首要责任乃培养本地圣职人员,先从较低的阶层开始,然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使能达成从这个民族中,给本地圣职生出领袖与主教,正因为是这样,如果现在不做,总也做不成。从前人们做的好或坏不必再管,过去的已过去了。然而现在请您许可您这最小的孩子,从他最可怜而又不堪之心的深处,充满信心地向您陈述,他对于今天之事的想法。 我带着千惊万恐,颤抖战傈,决定接触这个比以往更棘手的问题,因为这个伤痕现代比任何时候更鲜明。我并不是以我的名义说话,而是代替千万人说话,因着可赞颂的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爱,恳求您抛去长时期的作风,从惯例的屏障中走出来,放弃这成语:「勿超越你祖先们所设立的界限」;求您有理智的勇敢,面对真理,将真理探测到底,无论这种大胆的实际结果应该如何;请您最后决定这事时,不像是一个法国人,也不像是遣使会友,而只如同圣保禄、奥斯定、伯尼法、马尔定的继任者,或者更好是如他们当中的一个。 请对以上所说的,宽恕我的冒失。 在承咏『罗马的目的及普遍规则」是创立本地教会以后,在证实『欧洲越来越不能供给「必要」传教士的数目』以后,这就是说虽然罗马没有表明意见,而事实却在说明这力量有多么大,备忘录加上说:「结论是我们应该准备尽可能又优良又众多的本地圣职人员。「等天主上智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做罗马将指示给我们的事了。」 备忘录刚才正好承认了「罗马教廷已给我们指示了的」,而且数世纪以来不单单是指示(参阅宗教额我略十六世及教宗良十三世的文献),备忘录也证实天主上智就在这时候,以事实上不可抗拒的方式,向我们说话。由此观之,结论没有前题的宽大,准备优良及众多本地圣职只是「现行」程序的一部份,很重要的一点,而非唯一的一点。备忘录的这个结论或其类似的结论,虽然再三提起关于中国及整个远东的很多问题,但仍让我们传教区反罗马的现象保持原状。由于不重视这个问题,虽然很多世纪的传教士,流血出汗,而并没有如同初期的使徒及其继承人一样,建立一些教会,却只是形成一些精神殖民地,一个国家的殖民地,一个修会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是「在」教会内,而非「教会」。使本地圣职居于「辅佐」地位,常常是第二或第三等级的(我认识某代牧区,那里本地圣职的待遇还不如传教员的好)——他们在自己国家里,被看待如同外方人一样。 罗马愿意,积极的理由也赞成,在外籍传教士与本地圣职之间,对于种族问题,不该有一点区别。我们希望我们(藉着渐进的行动,明智而却实际和同意的演变)配合中国籍圣职。我们是否做到这一点呢?事实上,我们永久驻留下去的打算;我们甚至要把我们工作的园地,看成我们民族的,我们修会视为我们本国的「采地」;虽然损害人灵,我们仍坚持保留这些「采地」。不只是对本地教区圣职,我们不想退让,而且对其它各国和其它各修会,也是如此。主教大人,您知道,这不是一句空话,我可以很容易地举出许多具体和新近的实例。 明显地,我不愿说,外籍圣职该脱离一切并且马上放弃;也不愿说,修会能够立即撤退.而为更清楚地指出:在中国,我们的主教曾发表过言论,公开地说本地圣职现在不能继承我们,这等于说这个健康的人不能吃下一个大梨一样,『喉咙太小,食道要破裂,」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一下把梨整个吞下去,也不是等待天主上智使它溶解,而是一块一块地吃下。 主教,我跪着、伏首至地,向您说:您作主教三十年以来,教育了一些优良神父,有人跟我说,您也培养了一些学识渊博,和另一些才德卓越的神父。您是否从未想过呢?例如孙神父比所有的人都好,可以跟田主教或李副主教相比。徐神父可以做总铎。如果您怕欧洲的本会弟兄们不能允许他们属于另一种族的上司,这不是轻视他们吗?唉,什么?我们做神父的,为了爱耶稣基督的缘故,不能做许多欧洲世俗人,为了爱钱的缘故,在铁路、海关方面及在学校内所做的吗? 还有关于我们准备本地司铎,永远在准备辅理本堂。有人坦白地承认,这是他们唯一的目标,至少无限期地这样拖延下去。不只从一位主教,也不只一次,我听到说这个……但是不管关于未来有什么理论,而现在的实际而具体的理论不该妨害一种演变。虽然这演变是明智的,但也应尽量的快速(因为人灵在等待着呢,)向罗马很多次给我们提示的目标迈进。 传教区如果委任某某人作长上、总铎或副主教,「如同罗马数世纪以来所愿意的」,那会遇到什么危险呢?——还可以随意收回成命呀!这是为准备本地主教应进行的第一步,罗马等待我们推荐人已「望眼欲穿」了。因为天主没有我们的努力,不能救我们;教宗也不能把「一位没人推荐」给他的人,他不认识的小副本堂升为主教呀! 等待天主上智,等待罗马教廷,这句话若如此曲解,岂不是一个幻想吗?主教们等待罗马,而罗马已经很多次发表了它的愿望,更说明了它的意志,规定了目标,提示了主旨,指出了路线,罗马很自然地也企待着主教们。还有许多其它同样属于罗马圣部的事,罗马恐怕总也没有首先向我们谈过,为了这些,难道我们该期待一个「自动通谕」吗?就如北方的某些位主教,对于吃素和禁食的教规,若是最近没有申请很宽的豁免,他们到现在大概还是在吃鱼和蔬菜呢,而为很多其它的事也是如此。 但另外还有:教宗本笃十四世(参阅劳耐写的「李安德神父的日记」有一天以自动通谕任命刚在罗马晋铎的中国人郭神父为四川省的总主教。只是郭神父总没有被祝圣。恐怕那时的主教们要等待教宗亲自祝圣他。还有,传信部曾多次主张我们这里派遣一些修生到罗马去留学,「甚至负责一切费用」。我本人曾亲耳听到北方的一位主教很轻松地说,阴于传信部长高狄枢机的一次新邀请,人没有管它而寻找回答的办法。还有新近圣部又给我们下了同样的命令,而且更严厉,并指示将这命令在修院内向修生们诵读。或许认为有人被迫按字句服从,我怀疑有人赞成这种「想法」……可以引证一些其它的事实来清楚地证明,这样的等待罗马是一种幻想,因为罗马已经说过了,如果罗马的劝告不与我们内在的呼声相交流,没有世俗有成见人的回响,它的劝告没有实际而重大的效果。 还有: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去假定现在的本地圣职实在程度低,全部不适于任主教。这事实(并没有减低这句话的力量,「在这点上,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义务」),连是否有程度太低的事实,也值得讨论: (一)首先有种族的先决问题,使我们武断「如果把重任给本地圣职,会发生许多困难,必然处于党派及阴谋之中,如同本地的政府一样。」是否中国人本质上或遗传上根本不健全,不能担当统治的职务呢?这一定不是主教大人所支持的论调。这论调只适合于柯二文(注:是一位法国籍的的传教士,在数年前,曾在港出版了一本书,特别轻视中国人。)这里如同爱国问题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容易用不同的方式判断自己人和别人。 我们从另一角度观察:在意大利和封建的德国内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在波兰这方面已没有活力了吗?从一百年以来在法国,从最近几个月以来在俄国……真的,我们可以由于中国的内乱,而取得一个反对其圣职的结论吗?然而在其它国家,虽然比这里更多圣职参加国家活动,甚至政治生涯,但总没有从这争点上取得反对其圣职的结论。至于趋向组党及纷争乃人之常情:这种事在我读书于巴黎时,曾发生在遣使会会院;这种事也曾发生在我们军中,那时是和平时期,步兵与骑兵交战,骑兵轻视炮兵。这种事也曾发生在小小的比国(天主教的圣职及教徒在内)并且情况很明显,有一个比德国更灵巧的敌人几乎乘机扼杀了比国的独立。这种纷争的事甚至在教会内,以及各修会间也能有,且多次制造祸患,更多次还阻碍好事进行,但这并不使教会因此取治修会,也不使教会当局「由此争点」而阻止设立新的修会。 ㈡还有实际的问题,命令的词句太空泛,太普遍,人们各处可以听到说:『中国圣职不成熟,没准备好!』那里听到什么?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好呢?Servicre的神父婉转的说,关于他们的贞洁,很难建立基础;并且站在神修立场上还说:『对于这些被蒙住的眼睛,知道紫红颜色(指天主教礼服的颜色——译者)的效果吗?』——唉,不要如此说。人不知道,但似乎该试一试,对于没有蒙住的限睛,在中国和其它地方,人深知他的效果,这也该足够使我们宽大了…… 但我这个罪人,认识一些欧洲籍的主教,他们的品行没有什么可效表率的,他们的学识至少很平庸;其它的主教,他们的不谨慎甚至使他们的领事和公使们叹息,或者他们的行政使一个代牧区垮台。另外,他们也不会阅读,也不会写字,而只会勉强地讲一些,这也算了不起。我想不会有人因此推论欧洲人全部都不适合担任主教的职务,也不会有人对他们不放心。在这一方面,在「同一代牧区内」我见到一些中国神父,文学及教会学识都很卓越,就如何保禄及王保禄神父,王耀汉及更年青的赵神父,侯神父等等。我刚才指出姓名的这些人,都有超乎寻常的德行,其中一些人可做真正的模范,这是我在偶然的交谈中发现的。至于他们有否治理一个主教公署的能力,不能说他们可能有。因为从没有讨论过提拔他们,不过只知道他们都很完善地,也有些一人卓越地,达成了托给他们的任务。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中,除了罗文藻主教以外,我们有很多中国神父,他们由于时局所迫,在欧洲人不能进入中国的时期内,负起主教的一切责任心,而没有主教的荣誉,并且这是在特殊困难的环境下。四川的李安德神父就是如此,劳耐惊奇地谈论他说:「人们把他当做教区的领袖一样看待。」遣使会的薛神父也是如此,有些欧洲人写了他的传记,当做不可拒绝的见证。人们不能不惊奇这些中国神父们的德行,他们在战争的堡垒中,做没有袖章的负责领袖,来向一个外国人,多次比他们更年轻的外国人,每过一段时间,做他们的报告,而这外国人毫无学识,几乎连他们的国家都不知道。这些老资格的中国人等到头发白了以后,才获得一个最末等的位置,假若说中国人比欧洲人更倾向骄傲,正如盖尔闻藉圣经和教父所证明的,该认为这些神父己不是中国人,或者以为他们应该是圣人。 当我想到「我所认识的」某副主教,某主教,和我想起我认识的某中国神父;当我以具体例证想到,如果这代牧区的某中国神父接替某主教,某代牧区就多么好;我想到若这总铎区的某中国神父接替这里的现任欧洲籍的总铎,这总铎区就多么好……于是我不仅感到忧伤,而真是义愤填陶。当我考虑到这种局势不只是对罗马教廷,至少对其一切指导的明显想法,是一种欺骗、不服从,而且还是在远东阻遏圣宠活水的致命伤,阻止福音传播,妨碍基督所救赎的灵魂得救……是的,主教,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由此愿意闭口不言,保持中立,平安放心的匿迹在小传教士中不负责任,但这可能是个罪恶,一个真正的罪恶,并且我不怀疑天主在这事上要跟我算帐,当房屋起火时,该喊叫,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喊救火。 此外,如果种族的缺点,行政的经验不足等阻止我们,使我们犹豫不决,使我们过度明智,那末这里有一个不可了解的事实,就是日本。但愿主教大人不要跟我说这两件不相同的事。因为传教区本地主教的问题伸展到整个远东。所以,您看,一个民族,在半世纪中,做了一个奇异的事,唯一在历史中,使全世界震惊。现今在一切事上日本富到白种人的水平,在各方面受到平等的待遇,唯独我们所关心的一件事上反而例外:在日本曾有一位大官向一位天主教说:「日本实质上所抗拒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天主教。」如何证实这话呢?请看,在数十年之间,日本能产生打败苏俄的将领,与苏俄缔结和约的外交家,创办大学的教育家和有新发明的学者大科学家,等等;但在近乎三个世纪之中(在殉道者的教育之后,两世纪之久与天主教隔离——这是我的看法),日本没有能产生一位日本籍的主教。 对这问题,人总不能回答:也没有什么可回答的。这以坚强而有力的铁证,明确的理论,视为长久的耻辱,令人痛心:「因为主说,因了你们,我的名字在外邦人中受到亵渎……」 只有使慷慨的人「举心向上」,并该忠实地依据罗马教廷的思想进行改革。这可能是个名符其实的「皈依」,这为圣教会或许有圣保禄归化的各种效果……啊,主教,坦愿您肯作远东的圣保禄,施行了改革之后,那时必须对主题保守缄默的操行,只有藉俗气卑鄙而有趣的主题才引人人胜;它是错误和怀疑的根源;它使人武断更好的意念,因为思想是隐而不见的。是否可以相信宗徒们和效法宗徒的伟大传教士,不敢向他们的子弟说:「你们的责任重大,你们要加强读书的热心,修德的渴望,因为我们要给你们加委非常重大责任的时刻快到了,这重任我们只担当了一时。所以你们的圣德,不仅关系到你们个人的得救,而且关系到你们那里教会的兴衰,甚至你们祖国的富强。」宗徒和传教士认为他们必须隐藏那发生效力的语言吗?因为这是他们高尚情操不可置疑的铁证,也是在他们弟子心中,最能燃起保禄宗徒热火的论证。此外,人们平常都知道,有远大的目标能提高人的能力,也知道分担责任可以锻炼性格;相反的动作产生相反的效果。如此,头一部份的成果,由于这决定缄默,反而更远离我们一切行动应有的目标。对于类似「谨口慎言」的托词,是怕引起不好的气氛;熟不知好气氛乃是坦诚解说的罗辑结论,但行动与言语不一致例外。至于怕在这些可怜的中国人心中,燃起奢望,那为什么不为欧洲人证实这事呢?难道他们从生下来就适合荣华高位吗?有人要跟我说,因为这对欧洲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新奇事。我也很同意;但有人要求停止把新奇事展示在中国人前,但有一天终究该开始展示的。我们总不能有这么一天,这荣位为他们已不再是个新奇了,我们也不能许下将来有一个时期,到那时所有的人,对高官尊位都会感到厌恶,如同某些欧洲本会弟兄一样。 三、保教权 但法国公使要说什么?大使要说什么?政府要说什么?恐怕他们也不要说……甚至连他们这些人也发觉在这时候教权有废除的危机,恐怕他们也不能此葡萄牙国以前说的更多。此外,在这样严重,这样基本的问题上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事先已做了审慎的考虑,以及他们的合法结论,还可以预料到,他们的结论不能付诸实现,除非有损于保教权或摧毁保教权。为了圣教会的利益废除这保教权,为第一优先,而非将保教权之利益放在教会之上。 首先我们考虑教会由保教权已获得的,或者未曾获得的各项利益,然后对获有保教权的国家,我们该表示知恩。在这种假定下,我们的结论就是目前保教权可能是一障碍,从那时起。对传播福音,保教权就是一个人为的最大阻挡;所以必须使教会脱离这一保教权(这里决不先断定应采取何种方法,在步骤上也未想到应有何种谨慎和智能)。 现在由三种情况中选择一个:或者法国所做所为是为了圣教会的好处,或者法国为了对其本身自己的利益,或者法国所做是为了圣教会和法国,这两方面的利益。 在第一种情况下(只为教会好),法国已了解,他将不会同意,完全按照第一种情况,继续做这牺牲,因为这种牺牲已失去了它的意义。 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更喜欢向着法国发言,而不愿目麦示我们不知恩的危险。 在第三种情况下(双方有利),这种情况或许是真的。将来法国只能批准取消某一条约,这一条约在本质上因是暂时性的,而且只对某一方面(教会)有好处(若是真的有好处)。 有人说,既然是罗马教会当局接受了保教权,我们就应等待罗马方面亲自设法废除这保教权。我以为如此说法又重蹯幻想的覆辙,也就是我在讨论国籍神职时所提及的幻想。在这幻想里,淹没了我们的愿笙,并使我们感到轻而易举地不去究察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且这问题的解决可能很有利于圣教会,却损伤可尊敬的情感。怀这幻想就是寻找不负责的安逸。 这样做合法吗?我不以为然。若这问题的解决并不伤害我们,或者相反地,还近乎我们内心的想法,那我们就不这样说。罗马本身也曾遇到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的事。但当时法国的天主教信友和圣职人员,在政府考虑是否复交时,并未消极地等待着。这些人敢于讨论这问题,并在口头上和文字上做宣传。当时的人对他们的作风表示称赞。如果有人断定保教权仍然继续有用,或者仍然需要,以前过去的一切自然又要重加讨论。以我个人心中坦诚的想法,无论如何,确认保教权为某些一才俊之士是个进入教会的阻碍。我曾经由太多的人听说这话——他们这些人谈话代表一般人士的思想——他们当然并非先协议,使我发表这样的声明。而事实上,中国自顾不暇,中国的天主教也许畏惧教难,如怕类似近年来在法国发生的教难,或者甚至类似墨西哥的教难,或者类似英国在依利沙白女王时所发生的教难。假如有人作如此想法,我以为这等于是误解现在所有的中国人,认为他们大部份更愿在外国人旗帜的保卫下获得平安(曾有人举例说,中国人在突发变乱时逃往各租界;我认为这绝对不能混为一谈),一定这些人宁可遭到迫害也不愿意降低国格,他们在外教人中是优秀人才,明天在我们信友中也是卓越份子。 我在读到英国在宗教改革时期一些殉道者的传记时,深受这些贵族天主教徒的行为所感动。他们虽被撤职,打入监牢,但当他们听说西班牙皇帝派遣了一支舰队为替他退位的妹妹(或他女儿)报仇,并为恢复天主教徒自由。马上他们给国家的元首写了一封信,向这暴君表达他们感到外国的干涉对祖国构成莫大的耻辱,他们要求皇帝恩准他们能去攻打共同的敌人,而在战争后,他们要回到他们的监狱中。我感到这些榜样美好而又崇高。 以上这些都是反对保教权的作风.如果保教权实在与中国天主教的建立绝不兼容,,而且基督徒对于自己的国家有履行的义务,我认为为了获得保教权的废除,教友们该参与这场斗争,可庆幸的是完全没有人在旁协助反对,而且对中国教会,对法国也没有根本的和直接的阻碍。 英国的保教权,在某些基督教传教区,没有阻挡了教士们对鸦片作战,所以也没有阻止他们在两国之间的冲突中,不守「明智的中立」,而公开地决意为正义作战。他们更愿意把基督教,甚至把英国,从英国的错误中解救出来,这为基督教是个大利益,而为英国并没有伤害。 十三年或十四年前,反对美国人,抵制外货的时候,在北京有几位「美国籍」的基督教牧师领导反对美国的运动,在基督教的船中,甘目暴风雨的袭击.像这件事,没有比一个诚实态度的正直表现更适合的了。据我所知道的,美国的公使和代办对这事并没有表示不高兴,因为「在美国」牧师和基督徒同他们的中国弟兄唱调一致(在反对鸦片战争时,在英国也有同样的事)。这一切对英国及美国来说都没有害处;「相反地」,这除去了对他们的误会,因为中国人不需要英国牧师的演说,为知道英国的鸦片是坏东西,也不需要美国牧师的协助,为抵制美国的货物。但中国人所需要的是这种表示,为知道宗教不同于政治及商业。牧师们不同于领事,并知道他们对正义有一个清晰和极单纯的概念,来自民众而非来自司法部的概念。他们尤其需要这个举动,以便很清楚地认出做基督徒并不使人抛弃和减少公民的权力。 四、结论 主教,以上这一点点是我愿向您说的。这里没有将我的心愿,作充份的表达。我在主教大人前所感到的敬重及孝爱之情,及谦卑信赖的声音……这里不能充份的说出,只许可我给我证明我没有丝毫跟您隐藏那曾使我与长上不和的事。因为我所不提的(它太长,该写几本书……)是决定动机的部份,而非结论的部份。现在写结论,因为决议纪录在结论内;如果我不能如愿的,做为我长上们的安慰,「只」是因了这些结论。 人们所不原谅我的,就是由于我相信,为狡中国,尤其是在今天,外籍传教士不单该爱中国人,而且该爱「中国」,如同爱他的祖国一样,如同一个法国人爱法国一样。不原谅我的也是由于我时常在司铎,教友及外教人间传播这种「爱」。人们更不原谅我的,是由于我认为保教权有害于中国,更有害于教会,尤其由于我这样宣传过。 人们最不愿原谅我的,恐怕就是由于我以为,建立一个完全的本地圣职(主教在内)是我们的首要责任——由于教会的传统,罗马教廷的教训及事实上越来越清楚的呼声——也由于我曾在我四周努力传播这个观念,并表明,如果我能亲吻中国第二位主教的权戒,我将含笑九泉。 这就是该向主教大人说的那些,因为主教提供给我默想的「备忘录」不出乎这几点。以上是我在您这细心和慈父的意见前,我,这地下的虫蚁,灰尘敢写的。刘视察员最近来信规劝我更要与您的意见一致。主教,请原谅我,而我从我这可怜人的内心深处,我还敢说的更多,跪在您跟前,我敢向您喊说:「我在天主前,今天祈望,使您除了我带的锁链以外,完全像我一样……」(参阅:宗、二十六,29)。 假若您相信这祈祷是来自天主,如果您肯侧耳倾听,主教,那该多光荣,那该多有福,我多么喜悦我的苦难和「这些锁链」,但这是强大的攻势,决定性的一击! 天主晓得最近这几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事是非凡时;祂也知道这不是在外教的人海上,表面掀起的一些波涛,实际是个高深的亘浪。并且在天主前,在人前,我证实那属人的方法和那制造奇迹的思想——是的,主教,这是个奇迹——乃正是远东传教区的思想所反对的。罗视察员跟我说的很好:『我承认您总没有拒绝履行一个命令,您也没有不服从一个严格的禁令,但是您从来没有作一个服从的人。』如果这个谴责所能显得不合理的,我以为这正合乎要说的这句话:若我按字面服从,我就不能取得精神。罗视察员跟我说「老西开事件不算什么,而人们责备我的是我传教十五年……」也就是说:在这十五年当中,我没有在我心中接受,也没有实践我那些圣统上做长上的思想。罗神父有理。 罗视察员还说,杜主教、林主教前后也跟我说过:「放弃您与其它人们所有的区别,您满意您的职务吧,(好像该说:您要满意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看事时所站的角度),如此就完美无缺,您是位好传教士,您能做许多好事,等等。」有人希望已获得的成果仍然继续下去,而取消曾获到成果的原因——保留天主的恩宠不谈——因为有人不相信,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这完全像跟渔夫说:您捕到了更多更大的鱼,这很好,但请您要如同其它靠近河岸的人一样做,请您也在那里捕您的鱼——不要超过界线——不要在大海里撒网……而有人不愿知道这些大鱼不生活在河岸边,也不愿知道应该冒大海的危险,才能捕得满网的鱼。 主教,『撑往深处,撒网捕鱼吧!』逆风破浪,但要乘天主的风,并藉着群众的、深厚的、合法的、不可战胜的情感海潮,请大力摇船前进,驶往深处,请将您的小船紧随在伯多禄之后,作处女之航。多天,我们中国传教区的冗长多天已经过去了。请您相信,建立国籍的、生活的、丰饶的教会之时刻已来到了,这教会在群众中将是酵母,民族的肉体之肉体,「在基督内」成圣的血液之血液,唯一可行之路,并在希望中保有未来的预许。对这教会,我们已不该再做遥远的准备,而正是在最近的、决定性的、具体的准备中。如果我们愿意建立这教会,明智的、容易的、渐进的方法并不缺少!愿意就够了。 藉着彻底的牺牲,为可赞颂的基督,我们极可爱的救主,有人可以给教会保留现状的一切好处,而消除他的不利。一切为爱——爱天主,爱人灵——都是可能的。如果以您慈父的慷慨,您肯准许我,这个尘埃和灰土,您传教士中最末的一个,『恕我狂妄地说』,那我可以给您详细地提供某些办法。 啊,主教,再说一次,如果我这可怜的人,在这种精神中能思想、讲话及行动,我能在一块不毛之地,引发生命,如果您愿意,什么障碍您冲不破呢?为了向这民族表露我心中的这些愿望,我可以追随在这民族之后,您在手中,掌握着这些实现的权力,您本人什么不可以做呢?您在中国的主教们中最有资格,最受尊敬,天主要启迪您,藉您宗徒的伟大行动,和您伟大救世的及永远丰美的行动,使您的长久而神圣的任务得以完成。 主教,我在此停笔,但并没有写完,离结束还远,——参考书不够——恳求您原谅我大胆冒失,特别请您不要抛弃这卑贱的请愿书,这是用我的血写成的;也恳求您阅读它,不是用判官的眼,而是用慈父的心,看我跪着给您写这信,我双限注视着我的小十字苦像,它是天津一位殉道者的遗物,我有时因希望而叹息,也有时因恐惧而颤抖,热泪盈眶。 如果您在信中发现一些一不够润饰及不适于钧座的言词,请将它归罪于我的软弱及我的经验不足,但我恳求您,不要想在我心中能有当敬而不敬的情感阴影。天主知道我对钩座的孺慕赤诚。本教区所有的思想,就是在远东其它各地的思想;但是我未曾在其它任何地方见到一位主教,像您一样受到所有传教士们的敬爱,并且像您一样的爱护他们,我可以给他们证明这事;您如同一位慈父那么好,而且您也是穷人的、教友们的及教外人们的慈父;您具有的精神如同您的心胸那样宽大,并且准许我将我的心向您敞开。这一切及其它很好的事足以使人敬佩,因此在您的祝福下工作,感到很幸福,正是从我参观您的修道院和拯灵会修女院的最初几天开始,就使我感到痛苦;在参观的地方,每一步都可以见到您爱护众人的那些标记。当时我不停地想着:多么不幸,多么可惜,这里似乎什么都有了,除去唯一必要的,在建筑物上部缺少了装饰,更好说缺少了稳固这建筑物的决定性基础,缺少了使全身生活的精神;教会,「中国的教会」才能做到这个 !……那时我只是想这问题,而今天,比任何时期更迫切,由于我对钩座所有的孺慕之情,同样由于我对教会所有的孝爱之心,现在向您说出这个。 如果您在我的信中见到幻想和错误,求您告诉我,并准许我再向您讨论。因为对这样一个问题,审察的最后成果不拘如何,一定有更值得您这一位中国主教注意的,尤其您是主教团的主席。 请祝福您最不堪的孩子雷鸣远。 五、书后记 在我重读和在将这件信呈交给您的时候,我再一次对我的大胆感到恐怖。在我心灵的深处,我听到您召唤我,而我颤抖着向您回答: ——我并没有向您要求什么,这封信是什么意思呢? ——是的,您并没有向我要求什么,但这封信如同一个穷人的布施,来自人没有期待它的地方,如使它退让的地方。 ——然而,您不是我的谏官,也不是我的参议! ——不错,然而我是您的孩子,您的本雅明,是您以特别慈爱接受了的幼子,因为他相信在您心中有些权利。人都准许一个孩子爱自己的父亲,也让他跪着诉说他认为对父亲好的事! ——然而您是最后来到教区的。 ——是的,但是我的来此,却走了很漫长艰苦的路途,曾让我的血流在许多荆棘上,才到达了您这里! ——然而您向一个老伟教士说话,您却很年青…… ——是的,我也度过漫长岁月,好似数十年;再者,我总不比那个在米兰喊:「盎博主教」的孩童更年轻吧! ——然而,这在您以上,与您何关? ——这是为了我那中国外教的弟兄们,我向他们的父亲说话。 ——那末,您要记得你的身分。 ——当圣伯纳走出隐修院,对国王、主教和教宗说话时,有人也对这位圣人说过同样的话。 ——您的信完全彷佛在教训我,我仍然是您的长上, ——不错,圣保禄曾向圣伯铎做了这事,圣伯铎却宽恕了他. ——那末,您是自比圣人们了? ——圣人们在众人前基尼不拘这么多礼……我连传教士的名义都不配。但或许您可以收留我当作巴朗的可怜驴,主人比驴更有价值。或者把我当作救了加比乡勒的鹅群。但是天主不使我直到生命的末日常常做不能叫的狗。㈣ ——最后,您的使命在那里?您这样坚执,您的信号在那里? ——可惜,主教,因为我没有使命,我才向有使命的人来说话。随从大众是件好事,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大的。那位罗马的工头,历史上没有记载他的姓名,他没有求准许就喊出:「往绳上浇水(意大利文:在圣伯多禄广场,竖立埃及石柱时,栓柱子的绳子要断,有人喊:往绳子上浇水(广场上原是禁止人说话的),工程得以完成。——译者),罗马因此保住了他的石柱,这是重要的。如果打破惯例,我能希望中国的教会早生五十年或十年,由此使更多的人灵早日得救;我相信天主对于我不顾形式之罪,并不会追究的,也不仅我说了不习惯说的话。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