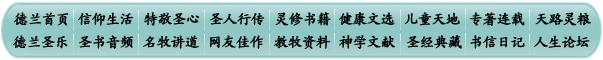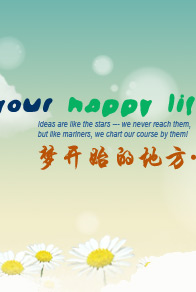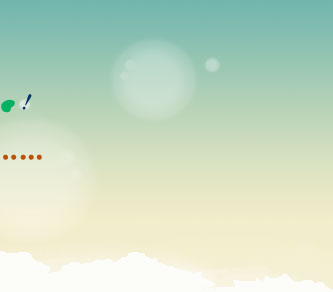在玛肋普的泉边,耶稣向众人发表了长篇教导。祂谈到天国的临近,语气带着紧迫:“人子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你们要趁着光明还在的时候,迎接天国的到来。”祂的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继续说道:“我就要离开了,剩下的日子数得过来。我劳苦的工作快要以一种痛苦的方式完成,但你们必须继续跟从我,和我一同做工。”
当祂再次预言耶路撒冷将要被毁时,声音充满痛楚:“那些拒绝天国、不肯悔改、只顾沉迷在世俗享乐里的人,灾祸一定会很快临到。”望着这片肥沃的土地,祂忧伤地说:“看这些表面上美好的东西,其实像装饰华丽的坟墓,里面却全是腐朽。你们应当察验自己的内心,不要让光鲜的外表遮住心里的肮脏。”祂一一指出他们的过错:贪婪、谋利、和外邦人不恰当的来往,以及对财富的迷恋。最后,祂沉重地宣告:“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繁华,最终一定会消失。将来在这片土地上,再也找不到以色列的子孙。”
祂隐约透露自己就是经上应许的那一位,将要应验先知的预言,然而能听懂祂话里深意的人,几乎没有。
教导的时候,众人分批过来听——老人拄着拐杖站着,中年男子低头沉思,青年屏住呼吸专心听,妇女用面纱擦眼泪,少女互相抱着哭泣。泉边回荡着阵阵哭泣声。
随后,耶稣带着门徒往东走了大约两小时,来到几处熟悉的农庄。附近小山上绿树成荫,是以前教导人的地方。从基提翁赶来的纳因门徒也到了,准备离开塞浦路斯。
耶稣在这里作了告别讲道,随后走访农家,医治病人。正当祂准备回玛肋普时,一位老农急切地求祂医治失明的儿子。那是一个十二口人的大家庭——祖父母、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家人。母亲蒙着面纱,把失明的孩子抱到耶稣面前。耶稣轻轻地把孩子接过来抱在怀里,用手指蘸唾沫轻轻抹在他的眼睛上,祝福后把他放下。当孩子开始笨拙地摸索,听着声音走向父母时,全家跪在地上感谢。耶稣把孩子抱在胸前,恳切地嘱咐:“要引导他走向真光,别让他的眼睛看见光明以后,心灵反而掉进更深的黑暗。”祂祝福了其他孩子和家人。人们流着泪,用赞美的欢呼声跟着祂。
在玛肋普那间专门用来聚会的屋子里,一场送行的宴席正在举行,人们围坐成一圈。穷人不但吃饱了饭,还收到了礼物。最后,耶稣以“阿们”这个词为主题,发表了一篇含义深刻的讲道。祂说,“阿们”是祷告完整的结束;人如果随随便便地念这个词,就是让自己的祷告落了空。祷告是向天主的呼求,把我们和祂连在一起,向我们打开祂的慈悲;而诚心念“阿们”,就好像亲手从天主那里接过所祈求的恩典。耶稣特别有力地说明了“阿们”这个词包含的大能,称它为万有的开始与终结。祂讲述的方式,几乎像是借着这个词,天主创造了整个世界。祂用“阿们”确认自己所教导的一切,确认自己即将离开,也确认祂使命的完成,并用一声庄严的“阿们”结束了讲道。随后,祂祝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众人哭个不停,依依不舍地喊着祂的名字。
耶稣带着门徒离开了玛肋普,巴尔纳伯和拿孙则在第二天跟上。他们从基提翁右边绕过,直接穿过田野、灌木丛和山脊。耶稣本想用纳因门徒带来的钱付住宿费,店主却坚决不肯收,于是这些钱就分给了穷人。所有现在或将来要从玛肋普、基提翁或撒拉米跟随耶稣去巴勒斯坦的人,将分开出发:一队从撒拉米东北边的港口过海,另外一些有事要去提洛的人,则直接从撒拉米动身。大多数受了洗的外邦人,都往革苏尔去了。
到了撒拉米,耶稣和跟随的人住进了祂第一次来塞浦路斯时住过的那所学校。他们从西北边进城,水渠在右边,犹太区在左边。我看见他们还束着腰,三个人一组,坐在学校前院的水池边。水池四周有一道小水沟,他们正在那里洗脚。每三人合用一条棕色长毛巾擦干。耶稣并不总是让别人帮祂洗脚;通常各人自己洗。这里的人早就盼着他们来,马上端上食物。耶稣在这里有很多忠实的跟随者,祂在他们中间教导了整整两个时辰。之后,祂与罗马总督谈了很长时间,总督介绍了两位渴望受教导和受洗的外邦青年。他们流着泪告明自己的罪,耶稣赦免了他们。傍晚,雅各伯在经师住所的前院里为他们行了私下的洗礼。这些青年将跟着哲学家们去革苏尔。
墨尔库里亚也派人来,请求耶稣在水渠附近的花园中和她见面。耶稣答应了,跟着送信的仆人到了约定的地方。墨尔库里亚蒙着面纱上前,手拉着两个穿着别致的小女儿。她们只穿短袍到膝盖,其他部分是一种精致的透明料子,上面装饰着羊毛或羽毛编的花环。她们手臂露在外面,脚上缠着细带子,头发披着,打扮得几乎像我们为圣诞马槽做的小天神。耶稣与墨尔库里亚谈了很长时间,语气慈祥又温暖。她哭得非常伤心,既为不得不留下儿子难过,也为父母把妹妹关在外面、任她陷在外邦的盲目里担忧。她也为自己的罪不停地哀哭。耶稣安慰她,再次向她保证她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两个小女孩惊讶地看着母亲,也开始哭,紧紧抱住她。耶稣祝福了孩子们,然后回到学校。
拿孙从基提翁赶来,由一位想跟耶稣去巴勒斯坦的兄弟陪着。
告别宴之后,耶稣和门徒来到约定的地点,罗马总督的仆人已经牵着驴等在那里。他们骑上驴,耶稣侧坐在带靠背的横座上,总督骑马在旁边。他们经过水渠,在城后渡过帕迪乌斯小河,走一条比沿海弯路更近的乡间小路。整个晚上景色很美,总督大部分时间都骑马在耶稣身边。前面一队十二人,接着一队九人,耶稣与总督稍微跟在后面,另有一队十二人走在最后。除了这次和圣枝主日,我从没见过耶稣用别的方式代步。天快亮时,离海边还有三小时路,为了不引人注意,总督向耶稣道别。分别时,耶稣向他伸出手并祝福他。总督下了驴,想要弯腰抱耶稣的脚。他深深鞠躬,退后几步又行了一次礼——我想这一定是当地的习俗,然后骑上马走了。两位新受洗的外邦青年也跟他一起走了。耶稣继续骑驴,直到离目的地大约一小时路时,祂和同伴们才下了驴,让仆人把驴牵回去。他们穿过一片盐丘,来到一栋长形的房子,一些水手正在那里等候。这里是海边一个僻静的地方,周围树不多,但沿岸有一道特别长的、长满青苔和树木的土堤。对着海的是盐场的住房和敞棚,一些贫穷的犹太家庭和外邦人住在这里。再往前,岸边地势稍陡的地方有一个小海湾,设有石阶通到水里,三艘船已经下锚等着。这里容易靠岸,盐就是从这里装船,运到沿岸各城的。
众人早就在这里急切地等着耶稣来。他们一起分享了简单的食物:有新鲜的鱼、金黄的蜂蜜、烤好的饼和当地的果子。这里的水又咸又涩,很难喝,人们会把一种野果扔进水里净化,然后仔细存放在陶罐和皮袋里。船员中有七位犹太人就在这儿受了洗,仪式用的,是一个擦得亮亮的大铜盆。
耶稣走遍了每一间小屋,安慰穷苦的居民,分发救济,也医治生病受伤的人。病人们向祂伸出无力的手,祂总是先温柔地问:“你们相信我能治好你们吗?"当他们坚定地回答:“主啊,我们信!”祂便伸手轻轻抚摸他们的患病处,使他们得痊愈。祂甚至走到长堤的尽头,主动去探访外邦人住的地方。那些外邦人起初怯生生地远远看着,但耶稣没有停下,祂走向他们,为那些光着脚丫的孩子们祝福,也耐心地给他们教导。
从纳因来的门徒早就到了这里,安静地等着另外两位同伴。他们按时会合后,三人就满怀使命地出发,先一步前往巴勒斯坦,去传报耶稣快要来的好消息。
耶稣一行共二十七人,在黄昏中登上了三艘小船。耶稣坐的是最小的那艘,船上除了四位门徒,还有几位船员。每艘船的中间都有围着桅杆搭的棚舱,分成几个小间,当作晚上睡觉的铺位。除了站在甲板划桨的船员,其他人多半已经进舱休息。耶稣的小船最先开动,我正奇怪为什么另外两艘船偏离了方向,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见它们在离岸不远的地方卡在了两片沙洲中间——它们慌忙点起火把,发出求救的信号。耶稣看见后,立刻命令船员调头回去。他们向第一艘船抛去绳子,小心地绕了一圈把它系好,又用同样的方法拉住第二艘。于是两艘船被稳稳地系在耶稣的船后面,安静地跟着前行。耶稣并没有严厉责备,只是温和地提醒那两艘船上的门徒:有信心固然好,却不能偏离正路;自以为是的代价,常常就是迷失。原来他们的船卡在了两片沙洲之间的暗流里。
第二天傍晚霞光快消失时,在靠近加尔默罗山脚、仆托肋买和赫法之间的宽阔海湾入口,耶稣的三艘船再次划到深水区——因为湾里正发生一场冲突:一艘大船和好几艘小船激烈地打斗。大船渐渐占了上风,甚至有几具尸体被扔进漆黑的海水里。当耶稣的船慢慢靠近时,祂站在船头,举手祝福了交战的双方。仿佛有一道看不见的和平临到,他们竟然慢慢分开了。没有人注意到耶稣的船队——它们静静停在湾口稍远的地方,像沉默的守望者。后来才知道,这场冲突是因为早在塞浦路斯时就结下的货物纠纷,小船特地在这里埋伏大船。双方站在甲板上,用长杆互相攻击,厮杀持续了将近两个时辰。最终大船制伏了小船,拖着它们慢慢离开。
耶稣在赫法以东、基顺河口附近上岸。几位宗徒和门徒早就等在岸边,其中有多默、西满、达陡、纳塔乃耳·苛塞,还有赫里亚金。他们一看见耶稣和同行的伙伴,就高兴地涌上前来,互相拥抱,问候的声音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众人沿着海湾走了大约三个半小时,渡过一条靠近仆托肋买、流进大海的小河。河上的长桥像一条坚固的空中街道,一直通到琴德维娅沼泽后面高地的后面。上坡之后,他们来到肋未城米沙耳的郊区——这地方和主城之间隔着一道弯曲的高地。郊区面向西边的大海,南边立着美丽的加尔默罗山和翠绿的山谷。米沙耳城只有一条街,一家客店横跨高地修建。在一口清泉旁边,耶稣遇到了前来欢迎的民众。他们组成节日的队伍,孩子们唱着欢快的迎宾歌,人人手里挥动着棕榈枝,枝头还挂着新鲜的椰枣。来自“水城”息曷尔-里贝纳特的西满,带着全家大小早就等在这里。他受洗之后,就搬来米沙耳住——因为他的孩子们一再请求,希望重新回到犹太团体中。这场欢迎仪式全是他自己出钱准备的,一心只为表达对耶稣的敬爱。当队伍慢慢走到客店前,九位来自米沙耳的肋未人庄重地上前,向耶稣致以诚挚的问候。